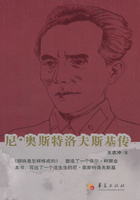
第4章 离散与团聚
柯里亚还没满9岁,但似乎比同龄的孩子要懂事些。
1913年初,他从乡村小学毕业,并且获得一张奖状。
不仅如此,女老师还特地登门,找柯里亚的妈妈奥里加,夸赞她生了个争气的儿子,说在学校里,柯里亚是优秀生,各门功课都得高分,而且品行良好,劳动积极,肯帮助同学……还真诚地建议:“这样聪明的小孩不多见,应该送他进城,继续求学。”
妈妈听着,又喜又愁,唯有苦笑,只能感谢老师的一片美意,送她到门外。
丈夫阿列克谢在外面找工作不顺利,大儿子尚未满师,没有工钱。仿佛雪上加霜,房东刚来过,说要他们家搬走,因为必须尽快卖掉这茅草屋。
怎么办呢?连吃住都大伤脑筋了,哪里还能考虑让小儿子继续上学的问题呢?
这房子虽然破旧,可毕竟租金低,一时上哪儿去租这么便宜的呢?
房东催得紧。万般无奈,母亲只得归还了房子,携儿带女,暂时到本村的一户邻居家寄居。当然,长住下去是不现实的。
两个女儿虽说都已有追求者,但年纪尚轻,还没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可如今家里遇到这么大的变故,不得不早些把亲事定下,两个女儿就这么嫁出去了。娜佳随同丈夫去了彼得堡附近,卡佳则前往基辅定居。
奥里加带着小儿子柯里亚,离乡背井,到老康士坦丁那边,才总算找到一份工作。
东家是糖厂老板。双方讲好了奥里加给他家当厨娘,工钱不多,但母子俩可以住在主人花园内的一间矮屋子里。
原本可以安定一阵子的,谁知人世间的事情变幻莫测,不久又出现了小变故、大风暴。
糖厂老板有个女儿,年龄跟柯里亚差不多。这女孩子不但骄气十足,而且嘴尖舌利,对同龄的柯里亚更是凶巴巴的,动不动就摆出一副小主人的架势,厉声呵斥。
那天,柯里亚独自在园子里跑来跑去玩。
“跑什么?滚开,这是我家的花园!”远远传来斥责声。
柯里亚抬头一瞧,果然又是这个厉害的女孩子,发辫上一只粉红色的大蝴蝶结,那颜色难看死了。头发油亮,衣裙崭新,满脸霸气,真讨厌。可妈妈叮咛过,人家是女孩,又是老板的女儿,千金小姐,得让着点儿,不能惹恼她。算了吧,柯里亚闷声不响,回到矮屋子里去了。
柯里亚总觉得憋气,仿佛肚子里包着一团火,他想找件事情做做,让自己平静下来。他拿起一张好看的画片,打算把它钉在床边空空的墙壁上。找到了小钉子,他刚动手要钉,千金小姐仿佛影子一般紧追不舍,跑了进来。
“别弄坏墙壁,这是我家的!”屋子小,小姐的喊声显得愈加尖厉刺耳。
小男孩气坏了,忍不住了:“你走开!”他一边嚷,一边扯住女孩子的发辫往门外拉。
一个拉,一个挣,缎子做的粉红色大蝴蝶结从发辫上掉落到地上,柯里亚恨得使劲踩了几脚。
男孩这样做的后果是,妈妈被辞退了。母子两人无处投奔,无处存身,吃饭睡觉,又全没了着落。
此时,奥里加接到来信,得知去了彼得堡的大女儿娜佳病倒了,同时得悉丈夫阿列克谢已在靠近边境的图利亚村的亲戚家住下,因为他在那边谋到了一份差事。她当机立断,托人把小儿子柯里亚送到他爸爸身边,自己则赶往彼得堡,去照料病中的娜佳。然而,当她再去寻找丈夫和小儿子的时候,却不知道父子俩被战争的飙风刮卷到哪里去了。
是的,人类社会刮起了一场特大风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场战争,参与的国家有三十三个,死伤人数超过三千万,更多无辜的百姓遭罪,颠沛流离,缺衣少食。
柯里亚刚到图利亚村爸爸这里时,倒也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自在的日子。
爸爸阿列克谢谋到一份护林员的工作。他年近六旬,饱经风霜,心地善良,脾气随和。发现附近的穷汉偷偷跑来捡干树枝,他也不会趁机暗示他们给自己塞钱。穷极的、胆大的甚至来砍树,他也不愿意处罚,不去逼人家赔钱。
那天,有个穷寡妇来拾干树枝,恰巧被林务官撞见,要罚款。阿列克谢傻乎乎地替她求情。林务官轻轻地冷笑一声,装作没听见;事后,说他护林不忠诚,毫不留情地把他开除了。他只得再去各村各乡找活干,维持父子俩的生活。
后来,他还为柯里亚找了一份放牛的活儿,于是,男孩子成了小牧童。
这样一来,柯里亚整天在树林里、草地上放牛,看绿树成荫,看青草连片,看碧空如洗,看彩霞半天。白桦树的挺拔主干,无花果树细枝的皱皮,松树木质球果的鳞片,都使小男孩遐思绵绵。他喜欢躺在草地上,将帽子枕在头下,闭上双眼,听鸟雀的啼啭,不知联想到了悦耳的民谣旋律,还是刺耳的喧嚣市声。爸爸还忙里偷闲,教他辨别多种鸟雀各具特色的鸣叫。
在这段似乎平静的日子里,爸爸曾患伤寒症。未满10岁的柯里亚居然镇静如常,悉心照料,使爸爸痊愈了。
1914年8月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持续到1918年。
阿列克谢父子所在的图利亚村,地处边境,正接近战线。柯里亚看到俄军部队途经此处,开往前线,而一批批难民从国境线上朝这里逃跑,再继续退向后方。
战线似乎日益靠近。大炮的轰鸣,震得茅屋砖房的窗玻璃格格直响;夜幕下,蓝黑色的天空一侧,被连连闪亮的火光映照得通红。村里出现了抬着担架的人们,而躺在担架上的伤兵血迹斑斑,有的还缺胳膊少腿。伤兵们痛苦的呻吟声在空气中回荡,柯里亚目睹耳闻,吓得心在震颤。
大批难民并不在此地停留,而是像潮水似的继续往后方奔涌而去。
数天后,本地的很多村民慌悚不安,也开始收拾物品,汇入这股汹涌的人流。愈来愈紧密、愈来愈迫近的炮声,促使阿列克谢父子也拾掇起衣物,融入了难民的队伍。
接连几个星期,这股洪流滚滚滔滔,往后方移动。人们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形容憔悴,茫无目标。
一路逃难的苦楚,在10岁的柯里亚的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甚至数年后,他偶尔还会梦见自己置身于难民的洪流之中,蓬头垢面,疲惫不堪;梦见愁眉苦脸的男人们牵着瘦骨嶙峋的马匹,拉动破旧而笨重的大车。柯里亚的耳畔仿佛又响起了妇孺的哭喊声,嘴里感触到涩涩的尘土味……
这天,他们到了舍佩托夫卡。阿列克谢觉得再往前跑,也不知到哪儿才算是个头儿,还不如就在此地停下。况且,这里是乌克兰南方铁路的一个交叉点,一个大枢纽站,找份工作或许会容易些。
柯里亚对舍佩托夫卡的一切都感到新鲜。车站上列车来来往往,旅客进进出出,络绎不绝,昼夜不息。机车库里,晚间也亮着灯,工作不停。这儿有许多工人,生活状况和言谈举止跟村民大不相同。这时,此地的嘈杂喧嚣与乡村的空旷寂静相比,似乎后者对小男孩更具吸引力。
阿列克谢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在火车站上当临时工,清扫月台和路面——但收入极低。
一家人分散了,父子俩单独过活,而且居无定所,异常艰辛。此时的柯里亚,衣不蔽体,头发乱糟糟的,鞋子也破了,久不见面的熟人简直认不出他来。
分散的一家人,在兵荒马乱的恶劣环境中,想尽办法,互相探寻。
不久后,哥哥米佳来了。他历经千辛万苦学成铁匠技艺,因此有机会进入机车库,先干杂活,接着很快就成了正经八百的钳工,不过工资还是很低。妈妈奥里加也来到这里和他们会合。
原本就是贫穷的家庭,如今兵荒马乱,流离转徙,一家人沦为难民。虽说刚在此地找了些活干,但晚间仍和许多难民一样,露宿街头,这总不是长久之计。何况已到了初秋时节,夜里凉意阵阵,似乎也在提醒人们,没有一个遮风挡雨的住处是不行了。阿列克谢一家非得赶快落实一个栖身之所不可了。
然而,战争像个恶魔,使整个国家受到重创,百物飞涨。奥斯特洛夫斯基家,除了两个已出嫁的女儿,四口人算是团聚了。父亲和大儿子怎么着也算是天天上班,有工资可领;妈妈也在想方设法接活儿来干,洗衣服,缝缝补补,挣些小钱。但父子俩工资太微薄,跟不上飞涨的物价;妈妈的收入不仅少得可怜,而且时有时无,并不稳定。
柯里亚人虽小,但见妈妈面黄肌瘦,他也知道疼惜。可这么小个孩子,要找份临时性的活儿也不容易。
爱玩是儿童的天性,柯里亚却不贪玩,他常常陪在妈妈身旁,见妈妈接的洗衣活儿多了,便帮着搓洗、晾晒。刚熟悉的当地小伙伴来招呼他去玩,他也往往摇头拒绝。
小伙伴恼了,拉腔拉调地喊叫:“洗衣婆!洗衣婆!”
他不发火,更不同人家争吵,似乎已懂得一点儿生活的艰辛、家庭的困难。小小男子汉,应该尽可能分挑担子了。好不容易找到事干,挣来一点儿钱,贴补家用,他就高兴得什么似的。
爸爸不得不辞掉工作,到四乡八镇去找活,但求增加些收入。
妈妈当前最大的心事,是要解决住房问题。购房,想都不必想;租房,根本交不起租金。
天无绝人之路。妈妈带着小儿子柯里亚在斯拉夫街发现一所小屋子,墙坍壁塌,破败不堪。经打听得知,房主觉得这屋子已经破旧得无法再住人了,就将它改成了畜圈,后来房屋继续损毁,似乎连畜圈也做不成了,房主不想再修葺,就弃之不顾了。而且,房主已经全家搬迁,离开了舍佩托夫卡。这个消息让妈妈觉得有了一线希望。
“我们就在这儿修盖吧。”她以一种拿定主意的口气对柯里亚说。
“修改?修改什么?”小男孩没听明白。
“修房盖屋!”
于是,母子俩大忙特忙起来。或者说,很多时候是妈妈一个人忙。柯里亚只要没在外面找到零活干,就帮着妈妈一起忙。大儿子米佳下班后也帮着干。丈夫阿列克谢则腾出几天时间来干活,他可是主要的技术力量。
奥里加在两公里外的一座荒坡那边找到了可用的黄土。母子俩合力提着破损的铁桶,硬是一桶又一桶地将黄土搬运了过来,然后和泥,修房盖屋。爸爸和米佳配合默契,把倒塌的墙扶起来,妈妈和柯里亚赶紧把和好的泥涂抹上去。修理门窗也主要是爸爸的技术活。
有意思的是,修房盖屋的设计师和指挥员不是别人,正是母亲奥里加。
秋意日浓,秋风渐紧,再也不能露宿了,必须加把劲,早日盖好居所入住,有时全家人从傍晚一直干到深夜。难,累,苦,可妈妈总是有说有笑,丈夫和孩子们便也铆足了劲儿,攻坚克难,直至浩大的工程基本接近收尾。大家心中都萌生出一种成就感。奥里加瘦削的脸上荡漾着满足的微笑,两句乌克兰谚语脱口而出:“兔子靠腿狗靠牙,各有各的谋生法。不怕万难,只怕孤单。咱们全家齐上阵,有了新屋子啰。”
房屋挺牢固,也还算漂亮,毕竟是自己千辛万苦修建的呀。
这天白天,妈妈独自在粉刷墙壁,接着又擦洗地板。突然一阵头晕发作,她知道自己太疲劳了。此时,在外打零工的柯里亚正好回来,抢过湿淋淋的抹布就擦洗起来。不一会儿,哥哥米佳也回来了,没脱鞋便要进屋。柯里亚把他挡住,说:“等一下,等地板干了再进来。”
米佳多半是累坏了,不听弟弟的,硬要进去。柯里亚气坏了,顺手把脏抹布朝米佳扔去。米佳身子一偏,啪的一声,抹布扔到刚粉刷过的墙面上,又随即落了下来。墙面上留下一块污渍,湿漉漉的,还有几条脏水正顺墙往下淌。妈妈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哎呀!”
柯里亚气极了,这是妈妈的劳动成果呀!小男孩扑到妈妈怀里,似喊又似哭地说:“妈妈,好妈妈!没关系的。我明天再刷一遍。”他转过头去,冲着尴尬地站在一边的哥哥嚷嚷:“你坏,你坏!”
“柯里亚,明天我跟你一起粉刷还不行吗?”
妈妈微笑着说:“对哥哥怎么能这样竖眉瞪眼的呢?全家和睦,胜过财富。你们哥儿俩明天一块儿干!”
新房子终于修盖成功。不远处,战争的浓云依旧滚滚翻翻。难民的洪流仍在经过这里,涌向后方。军用列车运载着新兵,到达此地便停靠下来,士兵们跑步上前线。运载伤员的车子则从前方退到此地,再往后撤。也有不愿意打仗的士兵成群结伙地撤退下来,和被宪兵逼迫挡住他们去路的增援部队打起来。子弹乱飞不认人,老百姓担惊受怕,都逃得远远的。在如此复杂而危险的环境里,他们一家四口居然能够团聚,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由于种种原因,父亲阿列克谢并没有经常和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同住一处,而大姐娜佳因病早亡,柯里亚实际上是和妈妈和二姐一起生活的。虽然阿列克谢没有留下任何提及小儿子的文字,但父子连心,二人一直保持着充满亲情的书信联系,小儿子的孝顺在书信中展露无遗。“未来先说”,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两封家书里摘录一些文字如下:
我亲爱的父亲:
我给你写信,我的慈祥的老人家,是要把自己的近况和将来告诉你……我常在你们的来信中读到抑郁的字句,诉说家里的贫穷困苦。我的心情不由变得非常非常沉重、憋闷……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向你们保证,你们只要再稍稍忍耐……情况会好转,我会给你们足够的资助。我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你们。我亲爱的老人家,我什么也不需要,我是共产党员,通通给你们。(此信写于1925年4月8日。此时,尼古拉21岁。)
爸爸:
你好!……今天汇去2000卢布,这是预付到1936年6月为止的、你的生活费……你一取到汇款,就把所有的钱存入储蓄所。只拿当月要花的250卢布……否则可能会被偷掉的……除了你的这2000卢布,我再汇去200卢布。你不妨以自己的名义给济娜和格利沙 ,让他们帮你做些杂事。传话给他们,只要他们关心你,我会奖励的……吃的方面,别舍不得花钱……(此信写于1935年10月。此时,尼古拉31岁。)
,让他们帮你做些杂事。传话给他们,只要他们关心你,我会奖励的……吃的方面,别舍不得花钱……(此信写于1935年10月。此时,尼古拉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