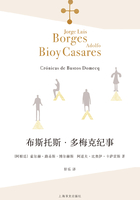
第1章 序言
献给三位被遗忘的伟人:毕加索、乔伊斯和勒·柯布西耶
每种荒谬现在都有了冠军。
奥利弗·戈德史密斯,一七六四
每个梦都是一个预言:每个玩笑都是时间子宫里的一份赤诚。
吉根神父,一九〇四
应某位多年老友和某位可敬作家之邀,我再次开始面对固执地埋伏在序言作者面前的风险与烦恼。说起来,这些东西倒没有回避我的放大镜。现在轮到我们像荷马描述的那样,在相对而立的两处险境间航行了。一个危险是卡律布狄斯:用很快会被正文内容驱散开的复杂蜃景去奋力吸引无精打采的、丧失了阅读意愿的读者。另一个是斯库拉:压抑我们自己的光彩,以免使接下来的文字材料显得暗淡无光,甚至被湮灭。只是,不可避免地,游戏的规则显然更加强势。我们就像收着爪子,避免一掌下去把驯兽员的脸蛋抓个稀烂的华丽孟加拉虎,遵循着序言这一文类的各种要求,但也没有放下批判的全部解剖刀。
读者一定会有的此类疑虑是不实际的。没有人会想把简洁的高雅、一剑探底的精准、杰出作家的宏大世界观与那掏心掏肺、老实巴交的散文做比较,后者就像是一个穿着拖鞋的老好人在一顿顿午觉间写出的值得称颂的、充满乡巴佬浑话和怨言的纪事。
有传言说,一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哲学家——出于良好的教养,我不能透露其姓名——已写好一部小说的草稿,如果没有变化的话,这部作品将被命名为《蒙特内格罗一家》,这一流言使我们原先写叙事文的、颇受欢迎的“丑八怪”[1],转身投向了评论界,不过倒不是因为他愚钝或是懒惰。我们就承认吧,这一寻找自己位置的英明举动得到了应有的奖励。除去不止一处无法避免的瑕疵之外,这本今天轮到我们作序的爆炸性的小书显露出了足够的价值。它的文字原料为好奇的读者带来了此种文类从来没有为人们提供过的兴趣。
在我们所处的混乱年代,负面评价显然已经失去了效力;它首先是一种不考虑我们喜恶的、对民族价值和本地价值的肯定,这些价值,尽管持续时间不长,却划定了当今时代的准则。另一方面,眼前这篇署名为我的序言是一位我与之经常碰面的朋友请求[2]我写的。所以我们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它的贡献上吧。带着他的沿海魏玛为其提供的视角,我们估衣铺[3]里的歌德开始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记录,一切现代元素都在其间震颤。想潜入小说、抒情诗、旋律、建筑、雕刻、戏剧以及各式各样视听传播手段这些为时代盖章的事物里做研究的人,都不得不撞见这本不可或缺的手册、这条阿里阿德涅的线,他会把它攥在手里,直至找到弥诺陶洛斯。
或许会有众声响起,一同指责中心人物的缺席,一位在高雅的概述中,可以将怀疑论者与运动员、文字祭司长与床上的种马调和在一起的中心人物的缺席,不过,我们还是不要将这疏漏归咎于嫉妒心了,尽管它是更合理的解释。我们就说是因为这位匠人天然的谦虚吧,他很明白自己的短处。
在我们正无精打采地翻看这本值得赞扬的小册子时,一次偶然的、对拉姆金·弗门多的提及瞬间驱散了我们的睡意。一种充满灵感的恐惧令我们困扰。这个人物真的有血有肉地存在着吗?他难道不是另一个拉姆金——那个虚构的傀儡、用自己高贵的名字为贝洛克的讽刺故事冠上题目的人物——的相似者或者回声吗?类似这样的烟雾降低了这份为人提供资料的作品的价值,因为它只应该追求保证——请您好好理解一下——诚实、朴素及流畅。
作者在研究巴拉尔特博士的六卷书册——这些书从该博士那不可抵挡的键盘上涌出,令人喘不过气,内容也没有什么价值——时,对团体主义概念的那种轻率态度同样难以被原谅。作者在各个组合而成的纯粹乌托邦中——那是那位律师的塞壬女妖所耍的手段——停留,忽视了真正的团体主义,而这种主义正是当今的秩序与更稳妥的未来的坚实支柱。
总之,这是一部并不算不体面的作品,还配得上我们用宽容的剑来拍拍它的背。
赫瓦西奥·蒙特内格罗
布宜诺斯艾利斯
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