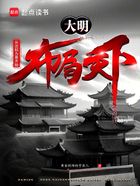
第16章 以武立身,喜得良才
刚还在纠缠的夫妻俩此时并肩站在小院空地上,恨不能找条缝钻进去。
不谙世事的小丫头晃悠着上前,好奇地睁大眼睛,看向初次见面的陌生人。
“少爷,这就是张五和他婆娘彩姑,还有他俩的闺女。”李管事说,接着瞪起眼睛看向夫妻俩,“还不快给少爷磕头?”
“啊?喔!”
张五后知后觉地跪在地上,“嘭”的一声把脑袋磕下。
这时,一阵沉闷的声音才姗姗来迟。
“张五见过少爷!”
在他旁边的彩姑更显得羞惭,急忙行了个不大标准的福身礼,说道:“我夫君不大会说话,请少爷莫怪。”
郑榕满不在乎道:“不必太过拘礼,我听说张五有一身好武艺,这次过来也是想当面看看,不如就在这练几招?”
彩姑是个精明强干的,闻言瞬间听出了郑榕的弦外之音,顿时又惊喜又忐忑。
“少爷放心,我家夫君习武多年,寻常人等绝对近不了他的身!”
她自豪地说,可一想起先前被少爷和李管事撞见的场景,又不由面上发烫。
见张五仍跪在地上,她连忙不轻不重地踹上一脚,这才让他反应过来。
张五爬了起来,身上带个鞋印,额头也全是尘土,看着狼狈,表情更显困窘。
只见他双手空空,不无委屈地说:“兵器不在家里,拳脚实在不算什么本事。”
郑榕眉头一挑:“你都会用什么兵器?”
“长短兵器都会用些,但要说功夫,还得是用刀。”张五不假思索地说。
“用刀?那好说,李管事,你也不用特地去取了。”郑榕扭头看向郑安,“把你的刀给他用用。”
郑安自然没有二话,取下佩刀就用力抛了过去。
只见那张五脸上瞬间没了先前的憨劲和懵懂,低喝一声,脚下奋力一蹬,接刀出鞘一气呵成,全身散发着凌厉的气息。
果真是个虎背蜂腰硬功夫的好汉,郑榕眼底闪过一丝惊艳,心里已定下七分,这确实是他想要的好身手。
“开始吧。”他面上不动声色地说。
“少爷,献丑了!”
张五握着刀,行了个江湖礼,接着便是狂风扫落叶般的刀法,阳光下的寒芒不仅让郑榕这种门外汉眼花缭乱,功夫在身的郑安也收起了眼中轻佻。
他凑到郑榕耳边,用只有彼此能听到的声音说:“少爷,这功夫不从小练个十几年绝对练不出来,我不如他。”
郑榕点了点头,视线落在小心翼翼站在不远处的彩姑身上。
这个持家有道,把丈夫治得服服帖帖的女人满脸紧张,视线紧紧锁在丈夫身上。
她知道,全家的未来都寄托在张五这身功夫和少爷的决断上。
若能得到少爷看重,也许自己这一家三口就能……
她又期待又忐忑,眼里闪着光,心底默默给丈夫加油鼓劲。
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张五对众人想法一无所知,只顾将武艺尽数施展。
一套刀法练完,他大气都不喘,嘴唇轻抿着,目不斜视,远看竟颇有高手风范。
可惜一开口就变回了憨直的乡下汉子。
“少爷,刀是好刀,可惜太轻,耍着不尽兴,可还有更结实的刀给我用?”
郑安惊得瞳孔微缩,这刀是他专门找人打造的,比寻常兵器重得多,未曾想到张五口中却还太轻。
郑榕也怔了怔,说:“那就给你打一把好刀。”说着抱起不怕生的女孩问,“你叫什么?”
“莺莺!”小丫头脆生生地说。
“呖呖莺声花外啭,好名字。”郑榕笑着望向夫妻俩,“你们是想搬去县里,还是跟我回浙江?”
这是改写命运的时刻。
张五还没反应过来,媳妇彩姑已高兴得眼泛泪花,飞跑过去用力抱住丈夫。
张五这才回过神,看着和自己相比小巧玲珑的媳妇,眼睛一酸。
他知道自己脑子不灵光,一身力气和功夫也没能真给妻儿带来好生活,平日里对媳妇百依百顺也是愧疚使然。
如今少爷赏识,不仅认可自己的武艺,还给了机会,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他用力搂紧媳妇,接着松开手,重重跪倒在地:“少爷既然瞧得起我张五,我们全家就跟定您了!”
话音未落,只听“嘭”的一声,又是一阵尘土飞扬。
郑榕满意地点了点头:“郑安,给他们家支二百两银子,再找人打一把够结实够分量的刀,都算我账上。回了浙江,把他们安排在我院子边上。”
张五激动得浑身发抖,二百两银子和一把好刀,对护院无疑是天文数字。
夫妻俩对望一眼,正不知如何谢赏,却见郑榕抱着女儿走上前,笑着说:
“你在家中行五而得名,未免敷衍,既然以武立身,改个同音的武字如何?”
“全听少爷吩咐。”
张五,不,应该是张武起身抱拳,眼中的色彩较刚刚更盛三分。
女儿莺莺也好奇地四处张望,突然张开手抱住郑榕脑袋。
“莺莺,不许无礼!”彩姑急忙呵斥道,不无紧张地看向郑榕。
郑榕却不以为意,轻轻松松逗乐了被母亲吓住的莺莺,看得夫妻俩更是感激。
李管事抓住时机说:“老奴这就叫人给他们收拾行李,跟少爷回去!”
“不急,还有件事。”郑榕把孩子交到彩姑手上,“郑安,挑些人带回浙江,愿去的每人每家免五亩地租。张武,到时这些人就由你带着操练,练出点样子来。”
“少爷放心就是!”张武声动如雷。
-----------------
郑安留在庄子里选拔护院和青壮,给郑榕随行护卫的任务自然落在张武身上。
家里有姨夫李管事帮忙收拾,他直接随郑榕回到蕲水县城。
一路上,腰挎长刀的他气宇轩昂,虽还是那身朴素打扮,却多了不少威风。
回到家,郑榕找人为他们一家三口寻了个临时住处,独自到母亲的小院,正看见她拿着自己来时那件穿久了的棉袍前后打量,一时心头微酸,唤道:“娘,我回来了。”
见儿子回来,刘氏放下棉袍,脸上的笑容顷刻间扩散开来:“回来的正是时候,一会儿该吃饭了。你那袍子穿久了,有几处地方磨得快要开了线,这两天娘给补几针。”
“针线活让怜珠做就是了,娘还是多休息为好,别伤了神。”郑榕说。
“你倒是体贴。”刘氏笑道,“你爹当年在翰林院,衣服破了不都是我来缝?先不说这些了,从那边回来有什么想法?”
母亲如此说,郑榕也不再坚持,说道:“咱家的庄子离码头不过十里,正适合建纺织作坊。此外近年北边流民越来越多,我想把他们也利用起来,学做织工。”
“纺织作坊……”刘氏沉吟着问,“还是浙江那个让你们父子俩闹心的改稻为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