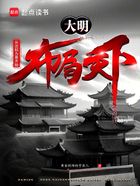
第27章 来者不善
二月十九,卯时末。
天将亮而未亮,一顶四人大轿缓缓进入钱塘码头,后面还跟着几十个管事随从,队伍浩浩荡荡,直奔停靠在码头中间的一条大船。
赶早出行或靠岸的商贾行人,只要在浙江待得久,都知道那是首富沈老板的船。
轿子停下了,宿醉未消的沈一石脚底下还有点打晃,身旁管事急忙伸手搀扶,却被他满不在乎地推开。
仍是那身布衣布鞋,他慢慢走向大船,带着商行的众人扬起风帆,驶离港口。
河风一吹,他的酒意渐渐消散。
看着两岸倒退的风景,他心绪激荡。
对自己被一个年轻人说服这件事,他是有些诧异的,不由得再次拿出那份琴谱,还有深夜再度醒来,挑灯完成的方案。
文士的雅,商人的俗,比肩而立,又交织在他的身上。
但不论是雅还是俗,不论是投其所好,还是真如酒桌所说合则两利,他都无法否认自己对这个计划动了心。
尤其在郑榕收下自己的织机和织工后。
他不是看不到潜在的风险——当地胥吏和大户的态度,改稻为桑顺利推行的难度,还有织造局这座大靠山的反应,他都想过。
但他知道,这是最好甚至唯一的机会。
欲望一旦萌芽,就一发而不可收拾。
错过了改稻为桑,再不会有这样大幅增加作坊和织机,向各地布局的良机。
商人逐利,逐的不是交给别人的利。
他也是人,想要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
面如冷铁的他收起了琴谱和计划书,抬头双眼望天,雨后的天幕渐渐亮起,身后是不断扩散的晨曦。
-----------------
沈一石出发了,在他走后不久,商行的一个随从将一张字条送到了郑榕手上。
简讯只有寥寥数语,郑榕阅后就将它丢入火盆烧成灰烬,披上外衣走到院里。
雨后的空气还算清爽,过几天就要出发返回湖广老家的弟妹们都在玩耍,有些已经把衣服都给弄脏了。
郑安和张武也带着护院们操练起来,从湖广带来的那十几个尤其认真,中气十足的呼喝声短促且规律。
“哈啊……也不知道老爹咋样了……”
昨夜又熬到挺晚才睡的郑榕伸了个舒展的懒腰,打着哈欠自言自语。
他能睡到自然醒,一起熬夜的郑泌昌还要早起,去总督府迎接“血雨腥风”的会议。
或者说,去看戏,顺便当。
事实也正是如此。
就像父子俩昨晚预料的那样,为了自己和背后大人物们的财路,也为了证明自己和郑泌昌这样的官场不倒翁不同,何茂才拿出了久违的精气神,与胡宗宪打起了擂台。
在他看来,这是据理力争。
和他站在一起的还有金华府、宁波府的两位知府,以及一个按察副使和布政司分管粮道的参议,最次也是四品官。
但总共不到半个时辰,这些靠着依附鄢懋卿,进而攀上严世蕃关系的官员就被现实洗刷了脑海中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狂热。
胡宗宪甚至自己都没出手,徐渭就拿出了年初查抄七家米行时收缴的各项证据,逼着臬台何茂才当场抓了那个参议,一队兵马径直开向他家,查封抄家一气呵成。
如此一套流程下来,在座众人无不胆战心惊,包括坐在郑泌昌下座的左右参政,何茂才更是又气又怕,脸色黑得吓人。
昨晚那一股被郑泌昌激起的豪气不仅荡然无存,甚至目光还多了几分异样。
胡部堂这等朝廷柱石,哪怕平日里显得再圆滑世故、和光同尘,终究也能稳坐巡抚总督位置七年,怎是自己能挑战的?
可世上没有后悔药,看着一直摆出事不关己姿态的郑泌昌,他突然感觉,或许是自己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这时他才意识到,且不说鄢大人和小阁老到底能不能制住胡宗宪,至少现在,他们远在京城,胡宗宪那一把沾了血的刀,此刻就悬在自己的头顶上。
他手上到底还有没有别的证据?这个问题没人知道,他更不敢冒险。
哑巴吃黄连的他也只能战战兢兢坐在位子上,再拿不出先前的蛮横与凶悍,活像个瑟瑟发抖的鹌鹑。
好在,毕竟是几个三四品的大员,胡宗宪也不是真打算斩尽杀绝——这样到了朝廷上太不好看,局面只会更糟。
眼见震慑住了何茂才的小团体,他也不再穷追猛打,继续议起正题,还特地点了郑泌昌的名,请他发表意见。
胡宗宪的嘱托,何茂才的求助,还有其他官员兔死狐悲的紧张,种种目光汇聚。
郑泌昌清楚,做好人的时候,到了。
“咳咳……”放下茶杯清清嗓,他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诸位大人,关于改稻为桑推行试点的方案,布政司……”
参议的事,似乎就这样过去了。
除了那张空空如也的座位。
而这场会议,也随着他轻描淡写的几句话重新定下一团和气的基调。
唯一不同点或许就是结束的很快。
晌午时分,郑泌昌就到了家,带着改稻为桑的最终方案,以及来自总督府的邀约。
此次改稻为桑试点由布政司统筹,杭州知府马宁远主理,布政司经历汪定瑜协理,郑榕则是因为没有官身,被胡宗宪赋了个总督幕僚的身份,与徐渭一同参与其中。
两天后,众人将会同台州兵马,走水路护送二十万石粮食赶往淳安。
而在那之前,四人明天要先碰上一面。
-----------------
对胡宗宪的安排,郑榕自无异议。
总督府外,迎接他的还是“熟人”徐渭和王书办,三人说笑着前往后堂。
布政司汪经历来得最早,刚见面就是一阵殷勤问候。
他是郑泌昌的老部下,跟郑榕也认识,算是有个照应。
寒暄几句,王书办回去迎接马宁远,郑榕拿出一包汪经历最爱的开化龙顶,引来徐渭半开玩笑的艳羡,一唱一和间,气氛热烈。
三人各自落座,虽是闲谈,一开口却还是公事。
作为半个东道主的徐渭率先说道:“眼看要去淳安了,这一走也不知多久回来,我等要和衷共济才是。”
汪经历附和道:“徐先生所言甚是,郑藩台也曾反复叮嘱。就是不知当地是何民情,国策推行又该是怎样的力度。”
“部堂说过,百姓大多是好的,推行国策是为了利国利民,守住这一初衷,事情就能办得妥帖。”郑榕轻声说。
“这是正论。”徐渭说,“每亩稻田一石两斗平价官粮,种桑图册也都要分发,汪经历责任重大。”
“这只是分内之事。”汪经历说。
郑榕接过话:“既要讲清利害,也要提供保障,更需予以帮扶,这样国策才能平稳施行下去,利国利民。”
“公子说得……”
“国策岂能这般温吞?必须雷霆手段,既要照部堂吩咐查清瞒报的田亩,更要以最快速度改成,这才是正道。”
几人正说着,门外走来的马宁远生硬地打断徐渭,脸色阴沉,直勾勾望着郑榕,目光透着嫉妒和排斥。
不等郑榕回话,他又讥诮地说:“公子毕竟还未入仕,说话做事难免天真。此去淳安,虽是部堂大人和郑藩台厚爱,命公子与我等共同议事,但还是不要负责什么具体事务了吧?”
两人对视着,气氛顿时尴尬起来。
徐渭的表情尤为僵硬。
郑榕眼底也多了丝冷意。
这场“碰头会”似乎有些来者不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