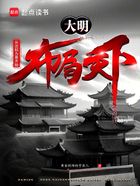
第6章 万家灯火,初遇胡宗宪
虽然说了不要送,但次日一早,郑榕还是在客栈门外见到了齐大柱一家。
身强体壮的齐大柱自不用说,他那调理多日气色见好,却仍显虚弱的媳妇也在,还有襁褓中呼呼大睡的齐睦。
好意难辞,几人便同去码头,依依话别。
船开出老远,一家三口仍站在岸边,直到顺江而下的航船消失在视野中才转身离开。
而在船尾的郑榕也正朝淳安方向远眺。
过了一阵,郑安前来禀报:“少爷,吴先生已安顿好了,船家也打了招呼。”
郑榕颔首道:“跟我折腾这么多天,你也去休息吧,我在这吹会风、看看风景。”
“我身子骨结实,陪少爷多待会吧。”没了外人,郑安便一点不拘束,笑着上前,“这齐大柱也真是个人物,功夫比我强得多。少爷既然瞧得上他,不如让他去老爷的藩司衙门亲兵队试试,以他的身手绝对没问题。”
“你倒是会替人着想,才认识几天,就开始替他说好话了?”郑榕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半带调侃地说。
郑安挠了挠头:“不是替他说好话,只是觉得,这身天生来的本事,若混个千户、镇抚干干,也算是不白费。”
“你说的没错,但还不是时候。”注视着雾气稀薄的江面,郑榕平淡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干的事,就像我到淳安调查,陆成去江西筹粮,齐大柱也得先留在淳安。虽然不是非他不可,但他确实是最好的选择,不能只盯着眼前这点事,要往远处看。”
郑安是个聪明人,不然也不会得到象征身世清白且受器重的主家姓氏,还能从小在府里跟着先生读书识字。
听郑榕如此说,他不再贸然开口,只侍立一旁,细细揣度着自家少爷的意图。
半月奔波,还真让他琢磨出了几分门道。
很快,淳安码头就只剩个小小的黑点。
-----------------
返程是顺流,本就能快上半日,再加上船家得了吩咐和赏钱,尽力之下,大年三十下午就到了钱塘码头。
沿途风景较去时增添了几分年节喜气,不时能听到两岸村落传来的鞭炮声。
等进到钱塘境内,场面就更上了一层楼。
作为杭州府和浙江布政司的治所,紧密相连的钱塘、仁和二县正应了史家那句“城内外列肆几四十里,无咫尺瓯脱,若穷天罄地,无不有也”的评价,不仅在江南,放眼天下也是一等一的繁华锦绣。
还没靠岸,就能听到往来行人的喧哗声。
新安江两岸人来人往,集市较往日大了数倍不止,人们或忙于置办年货,或急着给一年的大事小情最后收尾,更有人已开始为新年节庆做起准备——整个正月,追慕奢华的江南士绅都不会闲下来,商人逐利,自也不会放过商机,放眼望去,皆是热闹非凡。
郑榕还是那身青色棉袍,送别了归家心切的郎中,也不急着回府,带着郑安走进人流如织的码头粮市。
今天这里多了各式各样的摊位,还有不少江湖艺人,表演各自绝活讨些赏钱。
一年到头,普通人也只有在这几天才能摆脱一成不变的沉闷,为生活添几分亮色。
吆喝声、叫好声、嬉闹声,还有从靠岸时就没停过的鞭炮和欢笑声,共同构成一场无可复制的视听盛宴。
不觉间,小半个时辰过去,走出集市的郑榕包里已多了几样稀奇玩意,郑安则是背着行囊紧随其后。
身前是万家灯火,身后是众声喧哗。
正处在交汇处的他一时心生感慨,转头对郑安说:“我用白话吟两句词,你猜猜是哪位古人的哪首词,怎么样?”
“啊?”郑安脸色一苦,“少爷,我肚子里这点墨水你还不清楚?”
“早让你多读书。”郑榕露出一丝笑意,“猜对了,十两银子。”
“……喔。”很显然,郑安没太心动,只是不好扫了自家少爷的兴。
“那我念了。”郑榕清了清嗓子,声音清澈舒缓,“旧尊俎。玉纤曾擘黄柑,柔香系幽素。归梦湖边,还迷镜中路。”
郑安满脸问号,看得郑榕莫名好笑,正要说话,却听身后传来应答。
“可怜千点吴霜,寒销不尽,又相对、落梅如雨。年纪轻轻,怎的有这般感慨?”
沧桑沙哑的声线显然出自中年男子。
“尊驾倒有雅趣,不知……!”
郑榕好奇地转过身,话说一半,就触电般楞在原地。
他不明白胡宗宪这种大人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本能地行了个晚辈礼,用自己都觉得陌生的声音说道:
“晚生郑榕,拜见胡大人。”
-----------------
临街茶楼,二层雅间。
两个便衣亲兵和郑安守在门外,胡宗宪和郑榕则在屋里相对而坐。
“常听令尊提起你的事,不曾想居然这样碰了面,着实意外。这里不是衙门,我也没穿官服,叫我声世伯吧。”胡宗宪语气温和,全然没有封疆大吏的架子。
郑榕连忙起身倒茶:“那晚辈就僭越了,请世伯指教。”
胡宗宪笑了笑:“话还没问完,我看你年岁不大,这梦窗词里的愁肠从何而来?”
“回世伯的话,晚辈刚从淳安回来,在那里见识了一番民间疾苦,回到钱塘,看到眼前这般景象,心有所感,用的却不甚恰当,实在惭愧。”郑榕半真半假地说。
他自然不能告诉对方,除了这些,自己还想起了前世的家乡和亲人。
胡宗宪当然也不会猜到这里,眼中掠过欣赏之色,称赞道:“梦窗词既是思乡怀人,也有忧国之心,我看你用的再恰当不过。”
“世伯谬赞了。”
“你能体民间疾苦,便也能为民思虑,这是好事。今年是丰年,民生尚且艰难,来年未必有这般顺遂,岁岁年年,为官之人,须时刻临渊履冰才行啊。”胡宗宪语重心长,言语间透着提点和指教。
听话听音,郑榕当然晓得,毕恭毕敬地行礼道:“晚辈谨记教诲。”话音刚落,他又稍稍压低了几分音量,“改稻为桑的国策若是出了纰漏,世伯所忧之事就真要应验了。”
“什……!”胡宗宪先是一惊,紧绷的脸庞很快舒缓下来,目光多了几分探究,“这等军国大事你也知道。”
久居高位的威仪伴着话音扑面而来。
“世伯勿怪,请容晚辈禀报。”郑榕不卑不亢地说,“晚辈月初回的钱塘,从家父那里得知此事。国策乃是大事,容不得含糊,家父同样心有疑虑,便命我暗中调查一番,好做到心中有数、预先准备。所以我去了淳安。”
“哦?”
联想到郑泌昌最近的微妙转变,胡宗宪来了兴致,眼中多了些柔和与期待。
“说说看,都查到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