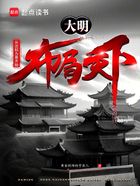
第8章 时值新岁,风雪将至
风起云涌的嘉靖四十年步步走近。
迷雾笼罩的棋局渐渐清晰。
一枚枚棋子被高高在上的弈手落下。
黑白交错间,血色浸染。
就在郑榕一家怀着心事却也其乐融融吃着年夜饭共迎新岁之际,千里之外的京城已是朝局震动。
腊月二十九,钦天监监正周云逸因天象问对激怒了嘉靖帝,责打廷杖时,被揣摩圣心的东厂提督太监冯保授意打死在午门外。
然而一整天过去,家中灵堂,披麻戴孝的老母妻儿却没等来任何一个官场同僚。
包括那些给他写信的人。
满城风雨,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嘉靖帝的罪己诏,以及将从正月初一持续到十五的斋戒祈雪。
靠近德胜门的小院里,一年轻官员坐在桌前写信,桌上摆着碗没喝净的白粥,上面飘着几根咸菜丝。
内阁和司礼监联署命令,所有在京官员年节期间不许升烟食荤,以分君父之忧。
高官们的大宅深处自然可以歌舞升平,奈何他这个入仕不久的翰林家境平平,还被欠了俸禄,能做的只有将信封塞得鼓鼓囊囊。
次日一早,这封长信就由邮传司的驿夫快马加鞭送出京城,一路南下。
相似的场景不止一处。
不同的书信以各自视角记述着近来京中的重要事件,抵达相同的终点。
浙江钱塘的书案。
他们都是郑榕的同乡和同学,早一步迈入仕途,往来依旧密切。
郑榕等他们的回信已许久了。
京城起风,浙江就要下雨。
把握风向是计划不可或缺的一环,哪怕他清楚记得每一个细节,也要拿到实证才有用。
-----------------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初十。
这天郑榕照例早起,打了套八段锦,身边是怜珠和笨拙模仿的郑绮。
一套打完,郑绮被怜珠领去前院——今天有场庙会,孩子们都想凑热闹。
略微出了点汗的郑榕简单吃个早饭就继续处理堆成小山的材料。
这十天除了拜年,他连堂会都没听,心无旁骛。
原因很简单,这事也只有他能做。
谁也帮不上忙。
古人眼里各不相干的大事小情被他巧妙联系起来,织成一张复杂的大网,将昏沉的迷雾缓缓拨开。
最多一两日,就该是水落石出之时。
半天过去,坐到腰酸背痛的郑榕喝了口已经冷了的茶水,用力伸了个懒腰。
“唔……真糟心!上辈子就过年加班,这辈子也不得清闲……”
正说着,门外传来轻响。
是带郑绮去庙会的怜珠。
“少爷刚刚在说什么?”隐约听到动静的她刚进屋就好奇地问,顺手添了热水。
险些被抓个正着的郑榕讪讪一笑:“没什么,就是肩膀有点酸,坐久了的缘故。”
“说了多少次,少爷就算用功也要多起来活动活动。”怜珠嘴上抱怨着,但还是熟练地捏起肩膀,力道恰到好处。
鼓鼓囊囊的信封被随手扔到书案一角。
“忙完这阵就轻松了。”郑榕言不由衷地说,伸手拿过信封,“这是第四封?”
“对,初七一封,昨天两封。”怜珠不假思索道。
“那就齐了。”
一目十行看完,郑榕满意地点点头,从抽屉里翻出先前看过的信件。
四封信摆在案上,薄厚不等。
怜珠虽好奇,却没多问,只是手上的力度更柔了些。
约一炷香的工夫,沉思的郑榕开了口。
“拿件衣服,我去老爷那一趟,午饭你就带着绮绮一起吃吧。晚上煲个汤喝。”
-----------------
距郑府几里外,浙直总督衙门。
四亩见方的大坪中间,三丈高的杆上飘荡着总督府的大旗,随风猎猎作响。
往日这里总是空空荡荡,今天却站满了挎刀执枪的兵将,面貌远非臬司和都司衙门那些只会欺压百姓的士兵、衙役可比。
从脸上隐约的肃杀之气不难看出,这里的大多数人都上过战场、见过血。
浩浩荡荡千余人紧张地沉寂着,他们都在等待从衙门里传出的军令。
整个浙江只有沿海抗倭的部队,尤其是宁绍台参将戚继光的义乌兵才有这种气魄。
但他们照理不该出现在此。
总督衙门后堂,胡宗宪独自一人坐在那张象征权力和地位的大案之后,瘦削的身形在这一刻被衬托得格外明显,尤其是脸庞。
这个年,郑榕没过好,他也是如此。
一手撑着桌案,抵在侧脸上,他静静地沉思了许久,直到自己的亲兵队长快步走来。
“部堂大人,”亲兵队长行了个礼,身上的甲胄发出清脆声响,“戚将军的一营兵马和总督衙门亲兵队已集结完毕,请示下。”
胡宗宪这才睁开眼睛,缓缓站起,手里多了份公文。
“出发吧,证据已经确凿,哄抬粮价、囤积居奇,你们兵分七路,同时查封那七家涉案米行,抓了他们的东家和各处掌柜,所有粮食登记造册,收归官仓,一粒也不能少。”
胡宗宪语气平淡,就像说的不是价值数十万两的粮食和至少几十条人命。
而且还要跳过布政司,真闹起来,恐怕有些不好收拾。
亲兵队长心头一凛,接过公文正要请示,却发现上面盖的不止总督衙门大印。
映入眼帘的赫然还有布政司大印。
困惑顿时涌上心头。
胡大人和郑大人不是……
军令如山,不容多想,他重重单膝跪地:
“属下领命!”
片刻后,披坚执锐的官兵排成整齐的队列开出府衙,直奔各自目标。
钱塘乃至整个杭州迎来了久违的震荡。
正月十五没过,就要见血了。
奸商的血。
还有某些不长眼的官。
-----------------
拿着四封京城来信的郑榕快步走进父亲的书房,一眼就发现了异样。
郑泌昌正穿着绯色官袍,旁边还摆着个硕大的木盒,郑榕知道那是布政司的官印。
“爹,这是怎么回事?”他问。
“还不是胡宗宪搞的鬼。”郑泌昌似笑非笑地看着儿子,“你喝了他的茶,他来找我要账了。七家米行,一百三十万石稻米,还有十几个大小官员,他要一网打尽。”
心头电流闪过,郑榕顿时明白了先前码头偶遇胡宗宪的原因。
他那不是体察民情,而是亲自走进粮市调查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事。
“原来还有这么一招……真是大手笔、大魄力。”郑榕由衷赞叹。
“你倒替他说好话了。”郑泌昌略带吃味地说,“没有你爹的官印,就算是他也别打算这么轻易地把事办了。”
“爹从来心明如镜,我知道您早看出此举的好处,所以才会帮他。”
郑榕毫不犹豫地给老爹戴起高帽,郑泌昌虽然心知不是这么回事,但还是十分受用。
享受了片刻儿子的吹捧,深知再多说几句就可能露馅的他赶紧转移了话题。
他也早看见了郑榕手里的信,问道:
“这些信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