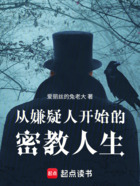
第21章 故事里的读者(下)
月光透过玻璃窗洒在工作台上,给晶莹的盐粒镀上了一层银辉。
叶延正在尝试制作出一份盐迹出来。
他没有急于联系雷斯垂德警探,而是在为破案提前做准备。
如福尔摩斯所说,此案的关键在于如何找到被刻意隐藏的证据,那么他刚刚得到的盐迹配方绝对可以发挥出大作用。
“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向苏格兰场推介盐迹。”叶延轻声自语,拿起玻璃棒和烧杯:“相信警探们会对这种能够追踪神秘痕迹的道具产生很大的兴趣。”
月光下,他将一份经过七日避光保存的纯净水倒入坩埚,加入新研磨的海盐。
随着火焰的跳动,液体开始翻涌,叶延低声吟诵着古老的咒语。
蒸汽升腾间,杯底逐渐析出一层洁白的结晶,其中夹杂着些许黑色颗粒。
那并非杂质,而是正在形成的盐迹。
叶延俯身仔细观察。
那些黑色颗粒中混合着一些真正的杂质,而另一些则散发着不起眼的微弱幽光,正与他的罗盘隐隐产生奇妙的共鸣。
是盐迹。
叶延小心翼翼地用银质镊子将它们分离出来,直到全部分离完毕,他最终得到了整整一小瓶闪烁着神秘光泽的盐迹。
“分离工作居然比制作还要耗费精力。”
他擦了擦额头的汗:“看来批量生产的计划要搁置了,除了咒语步骤,没想到辨别盐迹需要使用的能力会更多。”
窗外的月亮依旧明亮,叶延估算着自己的精神力消耗。
“今晚最多再做两批。”他揉了揉太阳穴:“否则明天就要头疼一整天了。”
第二日。
工作台上整齐排列着四个小巧的玻璃瓶,里面盛满了通宵制作的盐迹。
叶延疲惫的脸上浮现出满足的微笑。
本以为制作三瓶就是自己的极限,可随着经验的积累,他的效率竟超出预期,到最后还有富余的精力制作出第四瓶来。
带着四瓶盐迹,叶延返回家中。
进门路过信箱时,他顺手打开,发现一封来信正静静地躺在其中。
叶延拿出信,看向信封的署名。
“是若瑟夫的来信?”
他早在半个月前就寄了一封信到法国,只是一直没有收到回信。
和《福尔摩斯探案集》类似,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也是通过故事中一个角色的视角来叙述的。
这个角色就是若瑟夫·达尔芒斯。
叶延拿着信走进屋内。
说起来,他们也算是有血缘关系,两人如果见面,对方还要喊自己一声哥。
不知道在信里面对方会说些什么。
十几分钟后,叶延对照着法语词典将整封信给读完。
他的眉头微微皱起。
信应该是若瑟夫·达尔芒斯本人写的,这稚嫩的字迹很明显就出自于一个小孩。
但信的内容大概率是有人指导他写的,整封信夹杂着各种试探和奉承的话语,最后甚至在催促他继续寄钱过去。
“看来若瑟夫·达尔芒斯过得并不好。”
这一点叶延倒是有所预料,因此他寄出的信里还夹带着一笔钱。
菲利普诱骗原身自杀的事虽未败露,但他走私违禁品的罪行已被查实,政府因此没收了他的全部遗产。
想想原身父母双亡之后的境遇。
除非若瑟夫·达尔芒斯能遇到好心人收留,否则他的日子恐怕比原身还要糟糕。
想了想,叶延打算再寄一封信过去。
……
法国,巴黎。
若瑟夫·达尔芒斯已经不会再为自己的流离失所而感到伤心了,他逐渐习惯了这种被亲戚们当作包袱转来转去的生活。
他的行李很少。
一个破旧的行李箱,里面装着几件衬衫和裤子,学校上课用的书籍,一个日记本,还有一个小马玩具。
那是母亲送给他的十岁生日礼物。
每次被送到新的亲戚家时,若瑟夫都会攥紧那只小马,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觉得自己仿佛抓住了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
“若瑟夫,你暂时住在这里。”
姑妈冷冰冰的声音在狭小的储物间里回荡,她不耐烦地用手指敲打着门框:“记住,你得帮忙干活,我们可不是慈善院。”
他点点头,沉默地拿起扫帚。
两个姐姐早已出嫁,偶尔在家庭聚会上碰见,她们总是用扇子半掩着脸,声音压得极低,却又恰好让他听见。
“他又瘦又脏,像只小老鼠。”大姐嗤笑道:“真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轮流收留他。”
“谁叫他是我们的亲弟弟呢。”二姐漫不经心地摆弄着手套:“反正再过几年,我们就能把他打发去当学徒了。”
姐姐们谈论他时,仿佛他只是一件碍事的旧家具,而不是血脉相连的弟弟。
而学校里的日子更糟。
富人的孩子们穿着光鲜的羊毛外套,上下学都有父母来接,而他只有件袖口短得露出手腕的旧上衣,每天独自上下学。
以前的朋友们都不在巴黎。
新同学们都叫他“小乞丐”,有时候也叫他“乡巴佬”,往他的书包里塞死老鼠,或是趁他不注意时绊他一跤。
老师们看见了,也只是皱皱眉。
一个无父无母,从小地方转学过来的穷孩子,不值得他们费心。
若瑟夫学会了低头走路,学会了在挨打时咬紧牙关不哭出声。
夜里,他蜷缩在隔间的床垫上,听着老鼠在墙角窸窣作响,他数着天花板的裂缝,期盼着有一天自己可以快快长大。
他想念在哈佛尔生活的日子。
虽然哈佛尔的冬天很冷,但那些避之不及的眼神比寒风还可怕,巴黎永远只有填不饱的肚子,和永远不属于他的“家”。
若瑟夫感到很害怕。
他担心自己还没长大,就会像于勒叔叔一样被家人当作累赘,随便丢上一艘开往美洲的船,然后再也回不了家。
为此,他一直忐忑不安,直到那个改变命运的午后。
姑妈拆开了一封来自伦敦的信件,从里面滑出了一叠钞票。
[亲爱的若瑟夫,我的弟弟:
请允许我这样亲切地称呼你,因为我的确是你血缘关系上的哥哥。
我叫叶延,你也可以称呼我为纽曼·伊斯顿,我之前一直生活在海外,最近为了姑妈家的事情而来到英国,并了解到你的事情……]
信里面简单阐述了来信人的身份,以及他写这封信的目的。
姑妈兴奋得手舞足蹈。
她捏着信中的那叠钞票,用舌尖沾湿拇指,一张接一张地仔细清点着,而那封信则被她随手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若瑟夫等所有人都离开后,才偷偷捡起那封皱巴巴的信。
在煤油灯下,他看了一遍又一遍。
信中提到,自己的那位“哥哥”是从海外回来的,若瑟夫不知道海外有多远,但肯定离法国很远。
因为信里的句子有很多语法错误,像是查着字典硬拼出来的,生涩又别扭。
然而,这却让若瑟夫感到很开心。
他知道,这一定是那位素未谋面的哥哥亲笔所写的信。想到这里,一种久违的快乐在若瑟夫心中蔓延开来。
怀揣着某种幻想,他做了一个美梦。
梦中的他回到了哈佛尔,金色的阳光洒在细软的沙滩上,姐姐们提着裙摆追逐浪花,父母坐在不远处含笑望着他。
海风轻柔地拂过脸颊,带着咸涩而熟悉的气息。
就在这朦胧的光影中,他隐约看见一个模糊的身影正对着他微笑,那笑容温暖得让人想要靠近。
可好梦总是短暂的。
第二天,姑妈就强迫他按照大人的意愿回信:“若瑟夫,我亲爱的若瑟夫,来,坐到这里来,给你的哥哥写一封回信。”
姑妈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亲昵地吻着若瑟夫的脸颊,但他只感到浑身不适。
当听到对方要他写信的内容时,这种不适感骤然加剧。
甚至强烈得让他几乎要呕吐出来。
“我不想写。”
若瑟夫第一次反抗了姑妈。
他其实很想写一封真诚的信寄给那位关心自己的哥哥,信里面要写上他的高兴和感谢,以及期待与对方见面的愿望。
而不是那些充满算计的索求。
“若瑟夫,不要忘记了,是谁在供你吃喝,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好!”
“可是这样做是不对的。”
“哪里不对?”
“他是我哥哥,我给他写信不应该是为了索取钱财,那些并不重要。”
“不,你认为不重要的才是最重要的,若瑟夫。你还小,不懂这些,听话,只需要按照我们大人的要求来做事就足够了。”
若瑟夫依旧摇了摇头。
他从来不做自己认为不对的事情。
可最终,他还是屈服了,不是因为害怕挨饿,而是担心失去那匹小木马。
信被寄了出去。
自那以后,若瑟夫每天上下学都会检查一遍信箱,看有没有来自伦敦的信。
他既期待,又害怕收到回信。
若瑟夫害怕看到信中失望的话语,但他更害怕再次被抛弃。
半个月过去了。
信箱里没有再出现来自伦敦的信。
而姑妈也逐渐恢复往日的模样,不再给他的早餐里多加一个煎蛋。
若瑟夫每晚都会看一遍那封信。
他终于明白,为什么父母当年会对着一封十年前的旧信抱有那么深切的期待。
但他不是父母。
若瑟夫暗暗发誓,等长大了一定要去伦敦,亲手将自己真正想写的信,交到那个愿意称他为“弟弟”的人手中。
他拿出自己的行李箱,从中翻出自己的日记本。
日记本的第一页上写的是于勒叔叔的事情,那是他第一次对父母的所作所为产生怀疑,内心充满困惑时写下的文字。
而这一次,他打算写下自己原本要给哥哥叶延的信。
[亲爱的叶延,我的哥哥:
希望我没有用错对您的称呼,因为你在信中介绍自己时用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叶延,我大胆猜想,您肯定更喜欢别人叫您“叶延”,而不是纽曼·伊斯顿这个名字……]
灯光下,男孩的笔尖在纸上滑动,每一个字母都倾注了他最真挚的情感。
当在信的最后,写下自己的署名时,若瑟夫露出了一个开心的笑容。他蜷缩在小床上,抱着日记本进入梦乡。
这天晚上,他再次做了一个美梦。
然后,美梦成真了!
清晨的阳光刚刚爬上窗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若瑟夫。
“若瑟夫,快醒醒,你哥哥派人来看你了!”姑妈的声音大喊着:“赶快好好收拾一下自己!”
若瑟夫鞋都忘记穿,惊喜地打开门。
只见一位穿着考究的绅士正坐在沙发上,和他的姑妈亲切地交谈着。
“先生,您真的是我哥哥拜托您来看望我的吗?”若瑟夫的眼睛瞪得圆圆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
刚说完,他又慌忙解释道:“不,我不是在怀疑您的身份,我只是感到很开心。”
来访者摘下礼帽,露出温和的笑容:“千真万确,小先生。您的哥哥叶延先生委托我来看看您过得如何。”
听到对方准确叫出那个名字的发音,若瑟夫彻底相信了对方的话。
实际上,他也是练习了一个下午,才能够把“叶延”这个名字说得那么标准。
突然,若瑟夫像是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眼睛一亮:“请您稍等一下!”
他转身奔向储物间,光着的脚丫在地板上发出急促的哒哒声。
狭小的储物间里,若瑟夫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一直陪伴自己的旧皮箱,拿出那本记录着自己思考和希望的日记本。
当男孩再次出现在门口时,他的神情变得异常庄重。
“先生。”若瑟夫深吸一口气,将日记本郑重地递到访客面前,声音里带着一股期盼:“请您把它带给我的哥哥,这里面有我想对他说的话。”
访客微微欠身。
“你放心,小先生。”他的手指轻轻抚平日记本磨损的边角:“我一定会将它完好无损地送到你哥哥手中。”
若瑟夫正要发出感谢,却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未问对方的姓名。
“抱歉,是我失礼了。”
他意识到自己的冒失,脸颊泛起一丝红晕,局促地整理了一下过短的衣袖:“这位好心的先生,请问...请问您的名字是?”
访客将日记本放入内袋,重新戴上那顶做工精良的礼帽,遮住了自己的大背头:“詹姆斯·史密斯。”
他介绍道:“你哥哥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