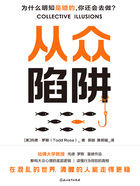
序言
榆树谷的秘密
折磨我们的,往往是想象,而不是真实。
——塞涅卡(Senaca)
纽约伊顿小镇,那座与邮局相连的假灯塔令人着迷,是以前叫作塔楼加油站的建筑物的一大遗迹。两层塔楼刷着红白相间的油漆,呈螺旋状,让人想到理发店的彩柱招牌。它窥视着这个坐落于纽约“肚脐”深处、只有几千人口的小镇。大约一个世纪前,灯塔静静地矗立在那里,见证了你未曾听闻的最重要的一次社会心理学研究。
1932年,一位来自雪城大学、名叫理查德·施恩克(Richard Schanck)的博士生来到这个小镇。当时,社会心理学还是全新的领域,作为该领域开创性的研究者之一,施恩克想研究作为个体的人是如何体验社群生活的。他之所以选择伊顿小镇(在其长达128页的博士论文中,他称之为“榆树谷”),是因为它是一个关系紧密的小型宗教社区,远离复杂的都市生活,人人都彼此熟悉。同所有小镇一样,榆树谷居民也热心地盯着彼此,坊间流传的闲言碎语悄然为每个人贴上标签。小孩放学回家路上摘了邻居的一个苹果,或者有人深夜匆忙回家途中被树根绊倒,肯定都会有人注意到。
榆树谷居民知道,施恩克来这里是为了研究他们的社会行为,但他们很快就把这位来自大城市的学者及其妻子当作了自己人。在三年的小镇生活中,施恩克夫妇同榆树谷居民们成了朋友,融入了这个社群。夫妇俩每逢礼拜日都会去教堂,因此,他们也受邀参加小镇上的洗礼、婚礼和葬礼,还受邀去参加人们的家庭晚宴。
施恩克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记下他观察到的小镇居民的行为。他询问他们对公共行为规则的看法——尤其是他们对教堂布道坛发布的各种社会禁忌的看法。
他问:“洗礼应该采用浸洗礼还是洒水礼?”
“礼拜日去剧场可以接受吗?”
“可以玩人头牌扑克游戏吗?”(源于新教徒仇恨英国王室以及嗜赌肮脏观念的一种禁忌)。在公众场合,答案几乎千篇一律:他询问的绝大多数居民都认为,即使是用人头牌扑克玩其他游戏(比如桥牌)也应该被禁止。
在榆树谷待了一年后,施恩克发现:榆树谷人和他们在教堂以及别的地方假装的那种人不太一样。他们公开宣称要如何如何去保持健康的习惯,私下却开心地抽着烟。他们还喜欢其他有“原罪”的乐子,比如喝威士忌酒、烈性苹果酒和杜松子酒,偷偷在家玩人头牌扑克游戏。
对此,施恩克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行为与意志相悖的现象?他们为什么会私下一套、当众又一套呢?
私下交谈时,施恩克请求他的新朋友们实言相告。为了弄清楚出现背离的原因,他问了他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永远改变我们对公众舆论的认知方式——也是直接促成本书问世的一大原因。
他问:“你认为,这个社区的多数人如何看待抽烟、喝酒、打桥牌?”
他得到的回答是:“多数人都会说,这些行为都是不可饶恕的原罪。”(1)
例如,77%的榆树谷人告诉施恩克,他们本人觉得玩人头牌扑克游戏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他们相信社区里多数人都赞成严禁玩人头牌扑克游戏。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自己其实就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接近3/4的榆树谷人都沉迷于这种“恶行”,但他们都秘而不宣。就连年轻而直率的牧师弗格森先生,私底下其实也是一个忠实的桥牌自由主义者,尽管他在公众场合对桥牌持有原教旨主义立场。
施恩克还向小镇居民询问了其他的宗教和世俗问题,包括是否应该和邻近社区共建一所新中学(争执特别激烈,甚至引发了斗殴),结果同样出现了类似的行为分裂现象。人们的公开意见和私下想法之间存在这种奇怪的“鸿沟”,让施恩克感到不解,他得出的结论是:人们采取多数人立场的程度,恰好是其他人认为他们是可接受的小镇成员的程度。但他们为什么遵循个体和群体都不喜欢的那些规范呢?小镇居民彼此之间怎么会存在如此误解呢?
就在这个时候,他意识到了一位名叫索尔特的孀居贵妇的文化控制力。她的父亲以前是弗格森所在教堂的牧师,因此,索尔特夫人自称代表着该教堂的历史和伦理规范。她也是该教堂最大的施主,弗格森先生得靠她领薪水。
索尔特夫人用她的铁腕控制了整整一代小镇人。凭借自己的个性力量,她规定着人们在公众场合要怎么做、怎么说。
“索尔特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女人,习惯对公共话题表达自己的观点。”施恩克写道,“人们经常听见教堂宣扬她的观点,然后就将她的观点视为小镇居民的代表性看法,根本没有评判到底有多少人会像她那样相信这些。”
然而,这位年迈的女士去世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就在她去世后不久的一天晚上,那位似乎是原教旨主义者的牧师和他的妻子参加了桥牌派对,当众玩起了人头牌扑克游戏。这个现象立即引发了一波闲言碎语,如野火般传遍了整个榆树谷。如果牧师能玩桥牌,那还有谁不能玩呢?人们在交谈中相互坦白,说他们也不反对玩桥牌。他们开始说出自己心中的疑惑:他们还在哪些事情上做错了?“魔咒”就此被打破。
理查德·施恩克总结说,榆树谷居民愿意听从索尔特夫人,是因为他们(错误地)相信她代表着多数人的看法。施恩克告诉我们:人们(哪怕是小镇上的人们)并非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彼此了解。他的研究表明:“音量高”的极少数人(在榆树谷只有一个人)可以轻易地代表和误导群体中的其他人。由此,他的研究让我们第一次窥见了本书的主题。
施恩克博士是最先研究我称之为“群体错觉”(collective illusion)(2)的学者之一。简单地说,群体错觉就是社会谎言。某个群体中的多数个体私下都反对某个想法,但想当然地认为其他多数人都接受这个想法,因而也接受这个想法,这就是群体错觉。个体服从他们所认为的群体需要,但最终谁也不需要他们的所为。这就是群体错觉的“黑暗魔法”。
最著名的群体错觉例子,是汉斯·安徒生1837年出版的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这个故事家喻户晓:两个骗子说服自负的皇帝,为他缝制精美的新衣。他们说新衣异常漂亮,但只有聪明人才能看见。自然,谁也不想被视为笨蛋,因此,即使新衣根本就不存在,每个人也都附和骗子。皇帝在城里巡游,趾高气扬、几乎一丝不挂。直到一个小男孩说出了真相,这个“魔咒”才被解除。
如果群体错觉只限于童话故事或宗教领域,那它就不会显得如此重要,本书也没有写作的必要。很不幸,情况并非如此。在当今社会,群体错觉无处不在,而且危险性越来越大。
当代人的普遍性误解
如果我让你定义成功,你会选择下面哪个答案?
A.成功是:追随自己的兴趣和才华,成为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里的出类拔萃者。
B.成功是:富有、职业光鲜或知名度高。
好了,你认为多数人会选择哪个答案呢?
如果你自己选择的是A答案,但认为大多数人会选择B答案,那你就是活在群体错觉中。
这个问题来自2019年的一项研究:我的“民众智库”(Populace)调查了5200多人,询问他们对成功的个人看法。结果发现:97%的人选择了A答案,但其中92%的人认为其他多数人会选择B答案。
这一发现还只是一个开始。为了让调查对象做出真实的个人权衡和选择,我们采用了规避社会压力影响的方法,结果发现:绝大多数人觉得,生活中最重要的成功标志是一些特质,诸如品格、良好的人际关系、教育等。然而,同样是这些人,他们认为其他多数人会优先选择财富、地位、权力等成功标志。
为了说得更清楚,我们来看看名气。在这项研究中,从76个备选的成功标志中,调查对象告诉我们,他们认为“出名”是其他美国人定义成功的唯一的、最重要的优先选项。但在个人层面,名气排名却垫底。
没错,私底下多数美国人对出名不感兴趣。但他们认为,在美国文化中,名气是大多数人的“北极星”。“民众智库”的这项研究结果很清楚: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追求有意义的、有使命感的生活;但我们同时也认为多数人的价值观和我们并不相同。因此,我们总是拧巴自己,尽力去符合我们以为的他人的期望。
个人成功并非“民众智库”发现的存在群体错觉的唯一领域。数年来,我的智库一直在关注各种重大的群体错觉现象,包括我们理想的生活方式、我们想居住的国家类型、对他人的信任度,甚至是我们对刑事司法、教育、医疗等机构的使命的看法。我们发现,美国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重要领域几乎都存在群体错觉。
“民众智库”也不是这个领域里的唯一研究者。近年来,学者们发现,全球各个角落、各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存在群体错觉。一切都染上了群体错觉的色彩,从我们对战争和气候变化的看法到我们的政治观点。它影响着我们对所有事物的态度,包括性别歧视、心理健康以及我们对身体魅力构成要素的看法。它影响着我们的道德行为,甚至影响着我们的食物选择。
例如,在美国,多数人都看重并希望利用雇主提供的各种家庭福利计划(弹性工作安排、资源转介计划、托儿补助等等)。然而,他们又认为大多数人并非如此。因此,受制于这种群体错觉,人们实际利用这些福利计划的可能性都较低,即使他们个人很想这么做。
不幸的是,群体错觉往往会放大人们的刻板印象。
在日本,大多数男性都想休陪产假,但认为其他日本男性大都不想休陪产假。因此,那些想休陪产假的男性休陪产假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在美国加州,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认为对方持有更极端的观点(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而形成了对政治极化的自我应验式的错误认知。大多数美国学生运动员都对学业成绩持有积极的看法,但他们认为大多数其他学生运动员并非如此。因此,他们对学习成绩表现得漠不关心,最后影响了自己的学习表现、强化了群体错觉。
仅在过去20年里,群体错觉出现的频率和影响程度在不断上升,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标志性特征。毫无疑问,它会带来深远的后果。
以政治中的性别代表性问题为例。尽管女性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一半,但她们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性别歧视(明显的答案)只是造成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事实上,“民众智库”进行的一项民意研究发现,79%的调查对象都认同“女性和男性一样能胜任美国总统”。(3)而且,女性参加普选——不管是地方、州还是全国普选——获胜的概率其实和男性是相同的。(4)
但如果你问:“女性和男性一样有候选资格吗?”一切就变了。原因在于: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讲,候选资格是你认为其他人会怎么认为,而不是你认为哪个候选人最能胜任。
例如,政治学家雷吉娜·贝特森(Ragina Bateson)发现:就个人而言,多数人并不关心候选人的性别。然而,一旦他们得知某竞选人拥有与其他竞选人相同的资格且为白人男性,他们就会压倒性地认定他最有候选资格。
鉴于我们“赢者通吃”的政治结构,选民经常玩这种凸显社会偏见的“谁赢”游戏。他们会认为:“我不是性别主义者,但其他人是,因此,我要投票给白人男性,因为我希望我的党派赢得选举。”这恰恰是群体错觉问题。事实上,你可能是地球上最没有性别歧视观念的人,但你对他人的误读可能会使你成为性别歧视的一部分,而你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这并不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已经显露出这个问题。在民主党全国大会召开前夕的一项民意调查中,“雪崩战略”(Avalanche Stratege)公司询问选民:如果选举当天举行,他们会选谁?
调查对象给出的选择依次为:1)乔·拜登;2)伯尼·桑德斯;3)伊丽莎白·沃伦。
然而,当被问到:如果他们可以挥动“魔杖”,让那个人自动当选为总统,他们会选择谁?调查对象选择了伊丽莎白·沃伦,她轻易胜选。
贝特森将这种现象称为“战略歧视”(strategic discrimination)。她解释说,这里的问题“不是对候选人的敌视。相比于直接歧视,战略歧视的动机是认为候选人的身份会让其他人不给他或她捐款、动员或投票”。因此,“美国人认为,白人男性候选人最有候选资格,其次是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再次是黑人男性”。
不幸的是,群体错觉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政治领域。对于我们社会生活中几乎所有重要的事情,它都会造成重创。你随便举一个对你真正重要的事情,我都敢打赌:你对大多数人的真实想法的看法,至少一半都是错误的。而这还是保守的估计。
群体错觉拥有巨大的破坏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它。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就必须了解为什么会存在群体错觉。
个人力量VS群体共谋
公元1世纪时期,罗马从圣坛上跌落,不再是一个令人引以为豪的共和国,转而变成了自私而堕落的皇帝们相继统治下的愤世嫉俗的专制帝国。罗马公民被专横(如果还没有彻底疯狂的话)的皇帝们压在其强有力的大拇指之下,他们发现罗马根本没有法治,只有自我审查。说错话经常会让人失去生计(很多时候甚至会失去生命)。因此,最重要的是自我审查——也就是说,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私下生活,但不能当众表达你的真实想法。
我想,1世纪时期罗马公民的感受,与当今我们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似的。
我们来看看伟大的罗马政治家、戏剧家和哲学家塞涅卡(Seneca)。
塞涅卡出生于公元前4年,此时正处于罗马始皇帝奥古斯都的专横统治时期,他还近距离地目睹了提庇留的暴政、克劳狄的偏执、卡利古拉的变态以及尼禄的自恋。皇帝们即使赤身裸体,他也能一一认出来。虽然塞涅卡不敢当面批评他们,但他创作的戏剧、散文和演说词对皇帝们的恶行起着“解毒剂”的作用,而对于这些恶行,皇帝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推动者、共谋者和顺从者。
塞涅卡是我愿意与之共进晚餐的历史人物之一。我发现他永远能激起我的兴趣,部分是因为他身上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受过良好教育的他是罗马最富有的人之一,却宣扬禁欲生活;他是智者,却未能远离宫廷阴谋;他是精英主义者,却谴责同僚们的失控的生活方式;他是实用主义者,却研究人类的情绪(也感受到了情绪)。
塞涅卡最为人熟知的,是他所写的有关斯多葛主义的著作,这种哲学为众人所摒弃,把它简化为一种默默忍受、压抑情绪的自我约束。(现在,如果有人甘愿忍受艰难的处境,我们通常就会称之为“斯多葛人”。)但塞涅卡的斯多葛哲学要比这更为丰富、深刻,也更实用得多。
同所有斯多葛主义者一样,塞涅卡也相信:消除痛苦的办法不在于外界,而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他认为,要想过上满足的生活,你就不应该压抑自己的情绪,而应该为自己的情绪承担起责任(他称之为“自我塑造”)。最重要的是,他表明我们拥有的个人力量和自主能力要比我们意识到的强大得多。
塞涅卡还指出,恐惧、怨恨、嫉妒、色欲和其他情绪刚冒出来你就屈服于它们,会带来自我毁灭的结果——他认识的许多罗马皇帝任性冲动,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因而这种见解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他给他的追随者提供了一个求知计划和简单可行的建议,以此来帮助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推断说,这样他们就不会被自己的情绪所控制。
例如,他说,害怕失去金钱的人,应该将自己的部分财富赠予他人,然后就会发现自己没有这部分财富也能生活得很好。他还给出了如何实现自我矫正的温和建议。塞涅卡认为,你不要为情绪失控而过度自责,相反,你可以晚上躺在床上,反思你屈服于恐惧、愤怒等负面情绪的那些时刻。接着,他希望你原谅自己。要知道,反思那些情绪爆发的时刻后,下次情绪出现时,你的自控力就会更强。(5)
两千年后的今天,塞涅卡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事实上,我就是希望你采用他的方法来反思从众行为和群体错觉。如果我们将他的“情绪”一词换为“社会影响力”,结果都是一回事。同情绪一样,社会属性也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大内在特征。盲目地屈服于其中任何一个,都是危险而有害的。塞涅卡的情绪控制方法,我们可以拿来解决社会影响力问题。
虽然社会属性是我们的生物学部分,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对社会本能的反应。用正确的知识和技能武装自己,我们就不必在做与众不同的人和做盲目从众的旅鼠之间做出选择。本书旨在为你提供必要的工具,让你真正理解我们为何会从众、从众如何表现、从众如何直接导致社会错觉,以及你应如何学会控制社会影响力而不受其控制。
为此,本书分为三个部分。
你可能熟悉英国前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提出的“第一洞穴定律”(first law of holes):身处坑洞中,就不要再挖掘。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为自己挖掘了一个大坑,系统性地彼此误解就是我们挖坑用的铲子。上篇“从众陷阱”讨论的是我们如何轻易就掉入了盲目从众的深坑——在这个深坑里,我们很可能不再自我思考,而是屈服于群体错觉。本篇讨论了三大陷阱,陷于其中,你就可能做出有悖于你的个人偏好或价值观的、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的错误决策。学会识别这些陷阱、采用几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你就会慢慢地获得自由,不再受所谓社会影响力的强烈影响。
不过,群体错觉依然会无处不在。在中篇“社会困境”中,我将讨论我们大脑的生物学局限是如何让我们屈服于群体错觉的。要真正驾驭群体错觉,就得理解它们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又是如何成为它们的共谋的。具体而言,我们社会属性的构成要素是模仿和比较,它们会欺骗我们,让我们追随过时的规范,误以为那些非主流的“大嗓门”——世界上的索尔特夫人们——就代表着大多数人。在本篇末尾,你将获得所需的知识武器,在更大范围内同群体错觉做斗争。
上篇和中篇包含的信息,你可用于个人生活。下篇的范围更广,涉及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重拾力量”将告诉我们如何驾驭社会的影响力,为创建一个完全没有群体错觉的世界做出贡献。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致力于两件事情:恢复自我一致与恢复社会信任。这样做,有助于创造必要的文化“接种”,确保我们社会运行体制中的群体错觉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满挑战:我们面临巨大的压力,为了归属感而应付、漠视或哄骗自己的个人信念。但盲目从众对任何人都毫无益处——它会夺走我们的幸福,阻碍我们挖掘个人和集体的潜能。
有了本书的助力,你可以避开那些导致群体错觉的从众陷阱。你可以做出更好的决策。你可以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更有成就感并最终造福所有人的生活。
每个人都是这个时代的共谋者
你上完厕所后洗手吗?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1989年一项研究的核心问题,该研究针对的是59名女大学生使用学校图书馆卫生间的情况。在一次实验中,31名女生上厕所时,研究人员待在卫生间显眼的地方,扮演观察者角色;而在另一次实验中,其他28名女生看不见研究人员。研究人员发现:当女生认为有人看着时,77%的女生会洗手;当她们认为自己独自一人时,只有39%的女生会洗手。
这项研究听上去虽然有些愚蠢,但它告诉了我们很多有关群体错觉的深层原因的信息。我们人类是彻底的社会性动物,哪怕只是意识到他人的存在,我们的行为也会发生改变。这种与他人保持一致的渴望——社会学家称之为“从众偏误”(conformity bias)——并非选择性的:它是我们根深蒂固的生物学部分。
例如,2016年,研究人员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fMRI),在被试者观看各种食物图片时扫描他们的大脑,这些食物包括西蓝花等营养食物以及糖果等垃圾食品。被试者看见某张图片后,立即被要求就个人偏好度评分,从“1”(不喜欢)到“8”(喜欢)。
被试者对某种食物给出评分后,接下来,研究人员向他们出示以前200名参与者的评分均值,如果被试者的个人评分与群体评分均值相同,就会出现“一致”这个单词。如果不相同,就会显示个人评分与群体评分均值之间的差异数字。最后,被试者完成所有的个人评分并获得群体评分的反馈后,研究人员请被试者对这些食物再次进行评分。
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再次评分时,被试者陷入了从众偏误,他们对食物的个人偏好度更接近于群体评分的均值。有意思的是,受影响的并非只有他们的行为;他们负责处理不同食物价值的脑区(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也被从众偏误改写。被试者一旦知道群体的偏好度,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就显示:他们的这个脑区从追踪各种食物的健康度转向追踪它们的受欢迎度。
然而,这些被试者不知道的是:那些群体评分均值完全是编造的——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操作,让被试者的评分显得与群体均值相悖。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表明了我们从众偏误的本质:事实并不重要。
更确切地说,我们的大脑会对我们所认为的群体想法做出反应,而不管这种想法是否根植于事实。
就像是地球持续而强烈的拉拽引力,我们对从众的渴望也是一种无意识的、几乎无法逃避的穿行于这个世界的方式——哪怕它完全是编造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但随时都可能误读他人,还可能盲从我们认为或期望的某种错误观念。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这种从众偏误使我们很容易成为群体错觉的猎物。
疫情期间,我自己就短暂陷入过群体错觉,加入了疯狂抢购厕纸的行列。一个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谣言,就让我这样的购物者抢光了超市货架上的厕纸,尽管北美厕纸生产商报告说供应根本没有短缺。可一旦人们跑去多购厕纸,抢购比赛就开始了。(6)
即使是在这种群体错觉期间,我清楚厕纸没有任何短缺,但似乎其他人都认为会出现短缺,因此,我无法控制自己。成千上万像我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行为,仿佛厕纸确实会短缺。于是,这种错觉滚雪球般地迅速蔓延。我们还没发觉,整个国家都在抢购和囤积这个东西,而且理由非常充分:超市的厕纸货架都空了!我还没发觉,这种群体错觉就已经成为现实。
社会学的一大核心原则恰好表达了我们相信群体错觉的情况。社会学家威廉·艾萨克·托马斯(William Isaac Thomas)及其妻子多萝西于1928年提出的“托马斯定理”指出:“若人们把情况定义为真实,则情况的后续结果也必为真实。”换言之,如果我和你都真的认为脸上长有雀斑并单脚跳跃的人是女巫,或者新冠流行期间没有厕纸可买,那这种想法的后果就绝对是真实的,不管这种想法本身是否基于真实情况。
由于从众性偏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大大小小的群体错觉的共谋。不过,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其他人也都在玩完全相同的游戏。我们内在的从众驱动力过于强大,稍不注意,我们就会把自己的个人判断扔出窗外。于是,我们都会集体陷入榆树谷那样的误解。
在社交媒体时代初期,“脸书”公司CEO马克·扎克伯格认为,新科技将开创一个多元主义和言论自由的时代。他在2019年10月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最初那几年塑造了我这样的信念:让每个人发声,就可赋能弱势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可推动社会变得更好。”根据这种逻辑,由于发声的人更多,群体错觉现在应该已经灭绝了。显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自普罗米修斯从诸神那里盗火之日起,新科技的故事就一直和意外后果密切相连。
今天,群体错觉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增强——在某种程度上,这要感谢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创造的奇迹。正常情况下,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任何人都可以做索尔特夫人所处时代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对榆树谷居民来说,误解来源于旧的宗教传统和当地的历史。相比之下,今天的社交媒体使得所谓的共识的转换更加便利,通过创造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多数人的印象,那些非主流“演员”就可以制造出群体错觉。
假如推特上有数十万个索尔特夫人,那你早就猜到了故事的结局。那些非主流声音让我们怀疑自己的判断力、认为自己没有和大多数人同步,有效地迫使我们沉默,从而加剧了群体错觉,我们成为他们的共谋。
在全国范围内,这些群体错觉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感:我们这个社会有问题。过去数年来,我们感觉自己仿佛陷入了某种怪异的、煤气灯光般昏暗的迷离噩梦。上下颠倒、左右难辨、对错不分。几乎一夜之间,我们社会的价值观仿佛都发生了改变。我们感到迷惘、沮丧、不满,彼此猜忌。我们问自己:是我们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还是两者都疯了?难怪美国人正在向信任开战,煞费苦心地构筑怀疑“城堡”,危害我们的个人幸福和国家繁荣。
在世界各地,民主正受到威胁,部分原因是各种社会问题通过法律或技术得到解决。毫无疑问,群体错觉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最大,因为社会要正常运转(更不用说要繁荣)就必须依赖这几点:共享现实、共同价值观,以及理解不同观点的意愿。这就是我将群体错觉视为人类生存威胁的原因。
坏消息是:我们每个人对正在发生的一切都负有责任。不过,这也是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有能力单独地或集体地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消息是:虽然群体错觉力量强大,但它们也非常脆弱,因为它们根植于谎言,通过个人行为就可以消除。借助正确的工具和明智的指导,我们就能摆脱群体错觉的诱饵。
我认为,我知道如何进行这种指导。
一旦屈服顺从,一旦人为亦为,
呆滞就会潜入灵魂所有灵敏的神经和官能。
她变得外表美丽而内心空虚。
——弗吉利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 非原话引用。——作者注(本书没有特别说明均为作者注)
(2) 历史上,学者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多数的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不过,我认为该术语不太恰当,让人困惑。处于群体错觉中的个体,其问题不是他不知道群体的想法,而是他认为自己知道但认为自己是错的。这不是无知;这是错觉。
(3) “民众智库”未发表的调研数据。“Project Delta 2.0 Results,”2020,7.
(4) 美国“反思民主运动”(“妇女捐赠者网络”发起的一个计划,致力于审视美国政治中的人口统计数据)对2018年美国大选所做的一项研究,调查了美国联邦、州和县层面的大约3.4万名竞选人,发现女性和有色竞选人获胜的比例与白人男性竞选人是相同的。
(5) 塞涅卡最厌恶的事情就包括盲目从众。他说,让自己毫无意识地跟随群体,我们放弃了我们的自主性,不但会伤害我们自己,还会伤害我们周围的人。由于意识到他所在的社会反复无常、缺乏道德,他喜欢引用一则伊索寓言:“我们不考虑道路本身是好是坏,我们只数脚印的多少,但这些脚印都不会走回来。”
(6) 1973年也发生过类似的危机。《今夜秀》主持人约翰尼·卡森随意开玩笑说厕纸出现短缺,造成顾客们恐慌抢购持续4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