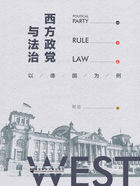
二 反政党的西方宪法思想具有认识论、政治哲学和历史背景原因
如前所述,英美法三国宪法的立宪与行宪过程,对于现代宪法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虽然这三国的立宪与行宪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但是在对待政党的问题上,至少在其行宪初期,却都殊途同归地走上了遏制政党作用、不承认政党宪法地位的道路。既然这些背景不同的国家都产生了相同的实践,在其背后自然会有一些具有共性的思想源头。人类普遍具有的思想倾向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这些被普遍接受的观点、理论,很有可能是一定历史时期人类普遍偏见的表现。有的时候,这些偏见甚至会超越特定的时空而存在,成为“人性的弱点”。从前文对三个国家早期立宪与行宪历史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对国家、人民的“整体性”的追捧,是否认政党这些由“部分”人民组成的政治小团体正当性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对此,本书将重点探寻整体论思想在人类认识论、政治哲学以及现代宪法兴起过程中的历史根源。
(一)人类的认识具有先天整体论的倾向
对国家和人民的整体论观点,其实有着更深层次的人类认识论方面的原因。在分析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时,康德提出了他的“概念的统觉的客观统一”思想。[52]在康德看来,人类的认识过程先天地就具有将各种直观现象统一在一个先天的自我意识之中的规律,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从整体上把握自己所面对的直观世界。因此,人类对于外在的经验世界,从认识论上说,就具有一个整体论的先验假设,即自己通过知性掌握的各种直观现象,最终应当是一个和谐的、统一的整体,而这种和谐的整体,本身是一个统一、和谐的自我意识在感性世界的反映。“我思”,是一个统一的、不矛盾、不冲突的“我”在思考,相应的,“我”面对的这个直观世界,最终也应当是一个统一、不矛盾和不冲突的整体。如果在这个直观世界中存在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些具有自己独立地位的部分,“我思”将无法统合这些直观现象,“我”也将成为一个矛盾的存在,但是这是先验的认识论所不承认的。虽然康德的“概念的统觉的客观统一”论是一先天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唯心主义认识论的一些缺陷,但是“概念的统觉的客观统一”论还是揭示出了人类认识的一种重要倾向或者说弱点。
政治生活是经验生活的组成领域之一,将康德的这种先天整体认识论思想运用于政治生活中,我们将得出类似的结论说,政治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最终也应当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否则,观察政治生活的“我”,最终将陷入自我分裂的幻想中。在西方经典宪法思想的兴起时期,政治生活的最大领域是各个民族国家,这样,作为认识对象客体的国家,更不应当陷入自我反对、自我对立之中。不过,人类的政治生活显然并不限于一国之内,国家之间的交往与活动,同样会具有政治意义,如果人们将整体认识论贯彻到底的话,应当认识到整个人类世界的政治生活都应当是一个整体,只谈及国家的整体性是不彻底的。
(二)整体国家观颠倒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
卢梭或许是对整体国家观最虔诚的一位支持者。卢梭的公意,显然正是这种统一、和谐的整体政治意志。[53]既然在公意中实现了整个国家、人民的和谐统一,那么国家、人民中的任何部分、团体,都是与公意的思想相矛盾的[54],这些部分、团体也将缺乏存在的正当性。至于像政党这样的,其存在目的就是将人民区分、切割成不同团体的“派系”[55],就更加缺乏其存在的价值了,甚至会是公意的敌人。
如果仅仅从纯粹思辨的角度来分析,卢梭的理论或许在理论上可以自圆其说。的确,当国家与人民、个人与社会已经实现了和谐的统一、融合之后,是不应该开倒车,又分裂出一些异质的小团体的。但是人们不能确定的是,卢梭的理论是否符合人类社会的活动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可以从真实的政治生活中寻找出一个超越于个别意志、个别利益的“公意”。
其实,在讨论“概念的统觉的客观统一”时,康德自己也就提出了知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区分。在理性认识中,范畴是可以完美地存在的,“我思”也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但是在知性认识中,直观都是不完美的,在经验中并不存在一个与范畴可以完美吻合的经验存在。所以,康德认为,他提出的知觉的客观统一,同样只是存在于主观世界中,是先天存在的。在康德提出的四个“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中,第一个二律背反就涉及对时空是否具有边界的讨论。[56]康德认为,在经验世界里讨论时间、空间的边界是没有意义的,只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因为,像整体、完美这种观念,只可能存在于理念之中,是理性才能把握的对象。借鉴康德的观点,我们会看到,卢梭的问题恰恰在于用纯粹的理论来限制丰满的现实,将经验等同于理论,最终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理论的虚妄和幻象。对于卢梭思想中的这种理性狂妄倾向,黑格尔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卢梭过于草率和简单地将个别、偶然的存在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现实中也造成了“最可怕和最残酷的事实”。[57]这些“事实”,应当就是我们前文讨论过的血腥的法国大革命吧。
如果说卢梭生不逢时,尚不及在国家的政治、宪法实践中落实、细化自己的整体国家观思想的话,那么施密特则在面对魏玛共和的乱象后,提出了自己在规范逻辑上或许同样正确而且更细密的整体国家观思想。在施密特的眼中,目前的国家已经成了一个“总体国家”,国家和社会具有了同一性。[58]当时的魏玛宪法也是以“全体德国人民同质而不可分割之统一体的民主思维”[59]“所有国家公民之意志同一性”[60]作为立国立宪的前提思想的。魏玛共和民主政治运作的根本目的,就是将“私我的利益与意见”“提升为统一的国家意志”。[61]当这一过程完成时,国家决断也将不再有“党派性”了。[62]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施密特认为,虽然当时政党在魏玛民主的实践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魏玛宪法并未以肯定的口吻提及有关政党的规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政党不是一个稳定的存在,其甚至是可以被视而不见的。[63]而且,由于活跃在魏玛共和政治舞台上的政党,实际上并没有践行着自由宪政的思想,没有起到将一个个作为个人存在的公民整合成统一人民的作用,反而成为一些组织稳定、具有相当向心力的小团体,对魏玛宪法实施产生着“切割作用”,因此,魏玛宪法实施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对抗政党的这种“切割作用”[64],以重新实现魏玛共和的统一与和谐。于是,在这种基于整体认识论的整体国家观中,为了追求理念上的和谐与统一,无论是18世纪的卢梭还是20世纪的施密特,都要求鲜活的政治现实必须服从于看似热情其实冷酷的理论要求,这是一种根本颠倒了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国家观。这种颠倒的国家观,不仅会在现实中造成严酷的后果,更会使得这些理论欠缺对现实的积极指引力。当麦迪逊已经指出,要消灭党派就需要取消人们的自由的时候,像卢梭、施密特这样的高度理想化的思想家,为了在实践中将其隐含着与现实严重对立的理论贯彻到底,就很可能会不惜取消人们的自由了。
(三)整体人民观中存在多数无法等同全体的难题
作为整体的国家,首先需要一个作为整体的人民。但是整体国家观对现实解释最乏力之处,恰恰就在于它无法解释在国家政治生活的现实中,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和谐、统一的“人民”,相反,人们看到的永远是各种各样的派系、团体,这些五花八门的团体拼织出了马赛克般的人民拼图。萨托利曾经指出,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人民”一词,都是指一个有机的整体。正是在这些国家,对国家和人民往往是以一种整体论的思维在讨论。虽然历史悠久的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评论》同样提到议员应当是公共利益而非其所在选区的代表,表现出了高度类似的整体人民观[65],但是“人民”一词在英语中却是有复数形式的,这使得整体人民观的思想在英美没有在欧洲大陆那么强烈。[66]但是人们无论在哪个国家在宪法和政治语境中讨论人民,其实都可以归纳出对“人民”的六种不同的解释,一个不可侵害的整体只是其中的一个理解而已。实际上有的时候,人们在谈及人民时,往往是谈论多数人罢了。对此,黑格尔也认为,“多数人”其实是比“一切人”更正确的用法。[67]此时,多数人与全体人民的关系、如何对待多数之外的其他人民,这些都是决定整体国家观实践生命力的关键问题。对此,卢梭[68]和施密特[69]都给出了相同的回答:牺牲那些少数人的利益,从而多数人的意志就等同于全体的意志。也正是在相同的逻辑下,西耶斯喊出“第三等级是一切!”的口号。[70]为了在实践中保证规范的自洽性,少数人,并且最终是公民个人已经不再重要了。需要注意的,这种将多数等同于全体、从多数人中创造全体的倾向,并不只存在于卢梭、施密特这些热忱的理想主义者的思想中。对于霍布斯这样的政治现实主义者,他给出的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创造一个全体的方法,同样是将多数人等同于全体,从简单的代数加减法则出发,让互相冲突的意见抵消后,剩下的意见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全体意见。[71]即使对于支持分权原则的洛克而言,他同样认为多数的意见与全体的意见应当画上等号。[72]于是,虽然这些思想家所处的时代不同,他们对于公民同国家的关系、国家的根本使命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认识,但是殊途同归地走上了将一个个鲜活的公民等同于冰冷的数字符号的认识道路。带来这种冷酷的理论结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就在于,他们在构造一个和谐、同质的整体国家、整体人民的过程中,在处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时,无法回答多数其实并不等同于全体的难题,最后只好以一种诡辩的方式将两者等同起来。这种诡辩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即使是在2017年的总统就职演说中,特朗普也不停地在“人民”与“一小部分人”之间来回跳跃,仿佛人民本来就应当是统一的,而这些特权阶级并不属于这个和谐的人民整体。[73]
(四)对整体人民观的推崇来自革命的现实需要
对于康德提出的纯粹理性的四个二律背反,黑格尔在讨论有限与无限的问题时进行了批准,并提出了自己的回答。黑格尔提出,其实在客观世界中,无限也是存在的,但是并不是以康德所认识的那种静态的方式而存在,而是以一种“无限”的发展形式,存在于一系列的“有限”的现象中。即,虽然就具体的某个时间、某个空间的现象而言,它们都是有限的,但是在这些现象相互之间,却存在无限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关系,最终表现为一个无限的统一体。[74]如果将这种辩证的无限观运用于政治哲学领域,我们将看到,如果人们试图在某个具体的团体之上,寻找作为整体的国家和人民,将犯下黑格尔所批判的强行将经验等同于理念的狂妄的主观错误。真正的整体、无限恰恰存在于这些作为团体、派系而存在的各种部分人民的永恒互动中。人民这个概念在许多国家的用语中都属于一个集合概念,或许也正反映出了在构造整体人民的过程中内在的具体的辩证矛盾逻辑。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早在19世纪初,黑格尔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这种辩证矛盾逻辑思想,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其后的法国、美国乃至德国的宪法实践依然以一种静态、部分的观点来处理人民问题。人们或许不可以简单地说,那些伟大的制宪者、革命者、思想家,因为见识的浅薄,没有想清楚我们这些后人已经洞若观火的问题。当人类在历史的转折点,执意选择某种具有缺陷的理论或者思想的时候,很可能是当时的时势所迫。这一点,尤其通过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表现出来。
早在法国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完全燃烧起来以前,“一致性”的思想已经在那些正在准备推动变革的法国人中获得了很大的支持。因为在改革派看来,只有借助于一致同意的原则,才可以反对国王以及他所代表的特权阶级的专制权威。[75]如果承认在人民内部存在某些与众不同的团体,特权阶级很容易就可以利用这种团体现象的正当性来主张自己的特权的正当性。例如,禁止强制委托原则的出台,就是为了反对当时将国家强制分割为不同的小团体的制度安排,结果使得人民被迫在一个个的小团体里听任特权阶级的摆布。[76]
而且,当时的革命主题在于将国家的权力从国王手中,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夺取到资产阶级的手中,至于这个“全体人民”是否存在,在这个“全体人民”的内部是否还存在部分人民,对于这些问题,革命者们是无暇且不愿意去思考的。其实这些充满激情的革命者,对人民抱着一种矛盾的看法。一方面,他们需要利用“整体人民”的可怕力量来推动革命的巨轮向前滚动;另一方面,他们又往往蔑视于具体的人民的认识能力和行动方式。[77]这种矛盾的态度,或许正是前述各位思想家在解决多数与全体是否相同的难题时,最终将公民贬低为冰冷的数学符号的反映吧。利用一个虚无缥缈的“整体人民”来推动改革和革命,即使是在今日的政治活动中,人们还是看到,这是一些政客,尤其是玩弄民粹主义的政党钟爱的伎俩。
此外,在革命的洪流中,革命的领导应当行动迅速、充满效率。[78]派系、团体之间往往无休止的讨论,看起来只会拖革命的后腿。一国宪法制定出来之后,本意往往是要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将宪法的主张付诸实践。但是不幸的是,在那些经典宪法的制宪过程中,制宪者往往真是那些心绪还没有平复的革命者。于是,这种革命的思维往往会被引入当时的宪法文本中,政党也就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当宪法得到稳定实施之后,这些革命时期的偏见和政治考虑的需要,也将镶嵌于宪法制度之中;如果宪法没有得到稳定实施,新的革命造就了新的宪法,这些偏见和政治考虑的分量就显得更加重要。于时,在这些现实的政治考虑中,整体人民观总是能够活跃在各个年代宪法实践和政治活动的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