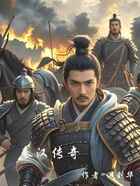
第180章 后记 二
第180章 后记 二
这是皇帝,再说臣子。
冯道生于乱世,皇帝轮流做,他岿然不动。因为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从二夫的传统观点,后世的人总是骂他。直到近人范文澜修《中国通史》时,还对冯道的政治道德大加批判。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没有人会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在那个王朝不断更迭的历史背景下,连手握重兵的武夫,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看到明天的太阳,我们怎么能要求冯道不事二主呢?
其实冯道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在朝中左右逢源、明哲保身,能够不做恶,救民于水火,已经难能可贵了!效忠于一家一姓,未必就是好人!如果主上昏庸残暴,做臣子的也要和他同生共死吗?
旧五代史作者薛居正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五代,知道五代为臣的不易,说法还算公道“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但下面转弯了,用了个然而。“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
新五代史的作者欧阳修就没有这么客气了:冯道自号长乐老还洋洋得意,不但算不得忠臣,且是一脸皮厚,不知礼仪廉耻为何物的家伙。
到司马光资治通鉴里,冯道更不堪了“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贰。此人道之大伦也”
司马光接着论忠臣:臣愚以为忠臣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对国家要像对自己小家一样尽心。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皇上有过错要力谏。国家败亡则要以死谢国。嘴上说说笔下写写当然容易。欧阳修、司马光出生在宋真宗澶渊之盟后,天下已平定,且宋仁宗是出了名的好人,所以他们才大唱皇上好,皇上棒,皇上好得呱呱叫。让他们活在五代试试,不知道会不会以死殉国。
到了元代,有位学者胡三省更对冯道加倍的义愤填膺,他说冯道——位极人臣,国亡不能死,视君如路人,何足重哉!
不过真是奇怪了,汉人在元代,已经是亡国之人了,这位胡兄为什么还活着呢?廉耻何在?只因为他不是宰相这样的人臣之极,所以就可以例外地活着?
到了清朝,就更不得了了。着名的思想家王夫之把冯道的罪行提高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度——冯道之恶浮于商纣王,其祸烈于盗跖矣!
真不知道冯道是怎样伤害了他,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资格这样评价冯道。满清也是外族,王夫之怎么不去死呢?
回到宋朝,伟大的文学家欧阳修、伟大的史学家司马光,他们一边在大骂冯道无华夷之防,无人臣之节的时候,一方面又把沙佗人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立为正朔朝代。也就是说,一边骂冯道不该给夷人打工,一边又承认夷人创立的江山朝代是合法的,真是不知道他们运用了什么样的标准,站在了什么样的立场。
按照他们的理论,冯道早就该死了,他至少应该死十一次,每一次皇帝更换,他都应该殉葬;尤其是面对耶律德光的时候,他应该横眉戟指,大骂不绝,然后引颈向刀,为民族留一段千古佳话,在皇帝的忠臣榜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话说石敬瑭称耶律德光为父,石重贵称耶律德光为爷。主子不要脸,凭什么要求臣子忠于自己?能避免或减少百姓死亡,那才是真正的英雄!
冯道微时曾有诗云:
莫为危时便怆神,
前程往往有期因。
终闻海岳归明主,
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
舟车何时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
狼虎丛中也立身。
全诗大意是说,身处逆境,不要怨天尤人,只要想一想自己以前做过什么,从而导致了今天的境地,就能够找到出路。在眼前这个朝代频繁更替的世界,夺得天下者就是明君,就可以前去事奉他,失去天下的就是倒霉的人,就要勇于离弃他。生当乱世,也绝不放弃自己的道德底线,但不必固执于一端。通往成功之路何止一条!往哪里走都是一片通涂。只要心存善念,就是虎狼窝里也能安身立命。
这里说的“道德”,也就是他自我评价的三不欺:“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而且是“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而三不欺集中到一点,就是先秦儒家所尊奉的“人心”、“民心”。这一点,冯道力所能及地做到了,也只有他做到了,而在那样一个“狼虎丛中”,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是佛、菩萨、圣人,其他的一切都不应苛求。苛求就是唱高调,就是假道学。
冯道虽然八面玲珑,游走于历朝的帝王之中,但他却是个典型的道德君子。他爱护百姓,怜惜苍生,不贪享乐。至于忠君,也要有可忠之君啊……唐庄宗,一个只知道听戏唱戏卡拉OK的皇帝,忠于他?那你得会唱戏。唐明宗好点,冯道也没有不忠于他啊。到李从厚,太短了,做皇帝才个把月时间。冯道跟李从厚还没树立感情呢。后面李从珂跟石敬塘皇位更替,一个唐明宗半子,一个唐明宗义子。清官难断家务事,还是皇族家务事,冯道管他干什么,谁做不都是你们自已人?而当耶律德光灭掉后晋,占领汴梁,蹂躏中原时,已外放做官的冯道主动进京。可他绝不是来争官做的,冯道此次进京,只是在尽己之能做些救人的事。
公道自在人心!不管后世如何攻击贬低冯道,当时因这一句话,中原百姓存活下来的数不胜数。当冯道死后出殡时,开封民众自发组织列队道旁,纸钱飞舞满天,路旁的树叶都成了灰色......
与冯道相比,大明的方孝孺就是个傻逼!冯道面对外族,尚且以百姓生命为重;而方孝孺面对的是明室朱氏子孙的夺位争斗,在胜败已分之际,他完全可以学习唐初名相魏征,另事新主,施展自己的济世才能,实现辅主治国的政治抱负。再不济,也可以学习李靖、李世勣等人,不掺和其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方孝孺偏要批龙麟、撩虎须,嘲弄、挖苦、讽刺和激怒朱棣。
1402年六月,南京城乱如麻。方孝孺静坐家中,等待被捕的一刻。
3年前,朱棣在北京起兵,以“清君侧”的名义,反对侄子建文帝的削藩政策。发兵前,他的军师姚广孝跪地嘱托,说南京城破之日,方孝孺一定不肯投降,希望不要杀他。
“杀方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姚广孝意味深长地说。
朱棣打下南京城后,方孝孺果然不逃,也不降。
下狱后,朱棣再三请人去劝降,方孝孺终不从。
等到朱棣准备登极时,为了借重方孝孺在天下士人中的名气,便要他起草登位诏书。
方孝孺身穿孝服,大哭上殿,见朱棣。
史书记下了两人的对话。
朱棣:先生请不要悲伤,我不过是效法周公辅佐周成王。
方孝孺:那成王现在哪里?
朱棣:他(指建文帝朱允炆)自焚,死了。方孝孺:成王不在了,为何不立成王之子为帝?
朱棣:国赖长君(意为朱允炆之子年幼,不适合掌国)。方孝孺:为何不立成王之弟?
朱棣:这是我们的家事,请先生不要过度操心。
说完,命左右上纸笔。
朱棣:登极诏书,非先生起草不可。
方孝孺写了几个字,随即掷笔于地,大哭。且哭且骂:死即死,诏不可草。
朱棣:难道你不怕诛九族?
方孝孺:便诛十族奈我何!
朱棣彻底被激怒,当场命人用刀割裂方孝孺的嘴巴,从脸颊割到耳朵。
方孝孺的族人、朋友、门生,一个个在他面前被处死,他都不为所动。
轮到他的弟弟方孝友,他罕见地留下眼泪,弟弟反过来劝他,“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
整整杀了7天,一共杀了873人.
最后才轮到方孝孺本人。他慨然赴死,并写了一首绝命词: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死时,年仅46岁。
这是中国历史上株连最广的一次惨杀。方孝孺,此后成为“骨鲠之士”的代名词,成为明朝最硬的“硬骨头”。
朱棣请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其实不过是做做样子,写不写都是一样!方孝孺偏偏不写,且扬言灭十族也不写!试问此十族之中,有何仇怨,而必令其与你同归于尽?朱棣与朱允炆,谁有资格当皇帝?父死子替,兄终弟及,都是前任皇帝在自说自话,本身就没有公理可言,却在伪命题中求解正义,结果肯定是缘木求鱼!方孝孺无端连累家人、亲友,以及知交、门生,看不懂有什么意义。
孟子曰:“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真正为穷苦百姓着想,不为名利,不顾成败,不惜生命的人才是英雄!
还有历代帝王的身边,总是离不开女人!
而帝王耽于淫乐,却顺理成章地将“红颜祸水”的帽子扣到她们头上。
有施部落最美的女子妺喜,利用夏桀贪婪自己的美色以及奢侈挥霍的特点,使尽浑身解数,让夏桀宠溺自己。
夏桀在她的诱哄下,沉湎酒色,干出“手撕全国绸缎”、“造美酒池以荡舟”、“在街上投放恶虎”、“施以炮烙之刑”等荒唐行为,尽失人心,大去国势。
后人都说是妺喜以自己的美色,将夏桀一步步地引向灭亡。
同样遭受千古骂名的苏妲己,如果不从她的角度看,你不知道她有多委屈。她花样年华,却被逼嫁给一个60多岁的花甲帝王。她强颜欢笑,便说她是商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而褒姒不爱笑,自从进宫之后从来没笑过;周幽王问她为什么不笑,她说她生来就不笑。
但她真的不会笑吗?
事实上她与青梅竹马的恋人在褒国时,她是会笑的;后来到了镐京,做了周幽王的妃子后,她想到自己的坎坷身世,以及像笼中鸟一样的“囚禁”生活,她就笑不出来了。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从褒姒的角度看,这是件十分可笑的事,她的笑不是高兴,而是苦笑!她是个被人拆散姻缘的可怜人,有什么高兴的?而且她即使不笑,周幽王也要亡国的!
所以“红颜祸国”这个词,不过是国家灭亡的借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