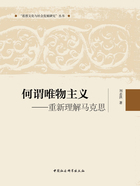
一 问题的提出
思想史上经常出现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思想史是纷乱的,缺乏规范和统一。哲学史尤其纷乱,缺乏规范和统一。仅以“最小”的概念为例。概念尤其是核心概念,是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大厦的基石。只有以含义合理明确的概念作为工具,才能准确清晰有力地表达思想。因而,理论必须赋予概念尤其是核心概念合理明确的含义。同样,对于读者来说,正确理解概念尤其是核心概念的含义是准确理解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一个基本条件。然而,在哲学史上,哲学家们甚至几乎没有对重要概念的含义达成过一致。同一个概念,不同时代、不同派别、不同哲学家经常赋予其不同的含义,甚至同一哲学家在不同思想发展阶段、同一思想发展阶段的不同著作、同一著作中的不同地方也时常赋予其不同的含义,致使哲学史上的诸多概念的含义相当多样。这正应了那句俗话:“同一顶帽子下可能有不同的脑袋。”并且,更为恼人的是,好像越是重要和常用的概念,越是难以统一和厘清其含义。哲学、形而上学、本体、存在、自然、心灵、理性、物质、实践等,哲学史上的这些重要概念无不如此。“哲学常常在词的定义等等方面纠缠不清”,[2]列宁相当精到地指出了哲学这一严重问题。对于这种混乱的局面,哲学家们负有不小的责任。哲学家们时常没有考虑概念的一般含义并说明自己赋予该概念的特殊含义就在自己新的意义上使用概念,造成概念含义的严重混乱。但另一方面,我们读者也有不小的责任。我们很少认真地思考和考察哲学家们所使用的概念的含义,往往自以为是地觉得这个概念的含义应该是怎样的,并就在这种未经考察的含义上理解这一概念以及哲学家们的思想,从而不能正确理解哲学家们那些有着特殊含义的概念,进而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哲学家们的思想。其实,哲学史上不少重大却无谓的争论正是源于对重要概念的含义理解和规定的不同。一旦澄清这些概念的含义并对它们达成共识,这样的争论也就自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想,众多重要哲学概念含义的多样和易变又的确具有一些客观与合理的原因。然而,这并不是给了我们一个可以推托责任的理由,而是增加了正确理解概念含义的重要性,更加要求我们必须明确每一个重要概念的含义。一句话,要正确理解思想,就必须正确理解重要概念的含义。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正是上述这个混乱大家族的一员。近代哲学以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成为了哲学王国中两个异常重要的概念。而在以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国度中,它们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和地位,仿佛具有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震撼世界”的力量。然而,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及其含义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争论不休、模糊不清。对于唯物主义的含义以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旷日持久的争论,罗素曾经风趣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唯物主义’是一个可以有许多意义的字眼……关于唯物主义究竟对或不对的激烈论争,从来主要是依靠避免下定义才得以持续不衰。”[3]在罗素看来,唯物主义这个概念具有多种含义,根据一些含义它是正确的,根据另一些含义它是错误的;然而,人们对唯物主义概念的这些含义的理解是不清楚的,并由此造成了关于唯物主义对错与否的无益的激烈争论。这番经验之谈启示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更令人惊讶的是,“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竟然斥责在我们看来同样是“百科全书派”“战斗的唯物主义者”代表的孔狄亚克是和贝克莱一样的唯心主义者。狄德罗批评孔狄亚克道:“他的原则与贝克莱的是一模一样的。按照这一位和那一位的说法……本质、物质、实体、基质等名词,是很难凭着本身在我们的心中引起理解的;此外,《人类知识起源论》的作者也明确地指出……我们知觉到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然而,这正是贝克莱的第一篇对话的结论,正是他的整个体系的基础。”[4]与此相反又相似,费希特在《知识学引论第一篇》中竟然说公认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典型——贝克莱的体系并不是唯心论的体系,而是独断论的体系。[5]而在费希特眼中,独断论对表象的解释原则和唯心论相反,认为彻底的独断论是唯物论。这样怪异难解的事情不能不让笔者产生这样的想法:把握唯物主义概念的含义必须认真研究每一位哲学家对唯物主义概念含义的理解和规定。
毋庸讳言,以现代学术规范为标准衡量,马克思著作的规范性也不是很高。同样以“最小”的概念为例。马克思对概念的使用也并非十分规范。除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少数著作外,他很少对重要概念的含义做明确的界定,从而不少重要概念的含义都不是明确清晰的;并且马克思还经常不作说明就赋予概念新含义以至于出现多种不同的含义。因此,和整个思想史一样,在马克思的论著中,实际上存在诸多看似含义一致却隐含着重大差别和分歧的概念。马克思思想的这种特点无疑给理解增加了难度,增大了误解的可能性,同时加剧了学者们理解上的差异。诚如德里达所言,马克思文本的歧义性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源泉。但是,它又何尝不会成为削弱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流毒呢?至少,它向我们提出了系统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的任务。任何简单的理解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正确理解马克思。因而,我们应该努力明确和澄清马克思重要概念的含义。系统深入地重新理解马克思重要概念的含义,是系统深入地重新理解马克思的重要一环。
在这些亟须重新理解含义的重要概念中,唯物主义是一个特别需要重新理解的概念。和唯物主义的含义在西方哲学史上问题重重一样,在显赫地位的表面光环之下,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含义也隐藏着严重的问题。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立场、原则、观点和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从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就始终是以坚定的唯物主义的面貌站立在历史和思想舞台上的。无论是创始人还是继承者,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几乎一致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的理论。马克思将自己的思想称为新唯物主义,恩格斯又将马克思和他的新世界观称为现代唯物主义。无须多言,正确以至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什么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的含义是什么?在笔者看来,对这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性问题,我们这些对唯物主义无比推崇的人的认识实际上一直很模糊。一百多年来,我们甚至没有独立地探究过这个概念的含义。对于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在马克思本人看来,什么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的含义是什么?亦即,马克思本人赋予了新唯物主义怎样的含义?在笔者看来,同样,一百多年来,我们整个马克思主义阵营实际上一直都没有对之作过准确全面的回答。21世纪的我们不能让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了。本书的目标就是要研究清楚这个问题。[6]
看到这里,一定有不少读者觉得笔者不是夸大其词就是迂腐可笑,不是发疯就是发傻!这个问题还需要考虑吗,这难道不是人尽皆知、耳熟能详的吗?唯物主义(包括新唯物主义)的含义不就是世界的本体是物质,意识是派生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外部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自然界是优先存在的等吗?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绝非没有丝毫讨论的必要。
首先,尽管人们一般遵从的教科书理解模式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处于正统地位,但对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实际上一直存在十分激烈的争论和交锋,诸多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和派别也有各自不同的见解。这些观点大致可以分成三种:恩格斯晚年的观点、列宁的观点和教科书理解模式的观点。恩格斯晚年认为,新唯物主义的含义是,现实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两方面)是思想观念的原型和基础,思想观念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和表现,并且他还自觉区分了新唯物主义和近代唯物主义的不同的具体含义。列宁认为,和近代正统唯物主义相同,新唯物主义的含义是可感物质实体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教科书理解模式认为,和以往的全部唯物主义相同,新唯物主义的含义也是世界的本体是物质,意识是派生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另外,还隐约地存在一种对新唯物主义含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这种理解认为新唯物主义的本质是历史唯物主义,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明确提出自己对于新唯物主义含义的观点,只是不同程度地接触和论及新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对新唯物主义含义的这种激烈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直至今日。
其次,以往的三种主要理解尽管不同程度地正确把握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含义的某些方面,但是都没有能够准确、全面地理解新唯物主义的含义。从而,在一百多年中,我们整个马克思主义阵营实际上一直没有准确全面地理解和把握新唯物主义的真正含义。毫无疑问,对于这样一个十分重要、有各种不同观点但并不准确、全面的问题,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对它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得出我们所认为的正确观点并以之分析和评价以往的各种观点。
需要在此说明的是,本书把传统教科书的观点作为主要论战对象,打算在分析和批评这种正统观点的过程中揭示和阐发新唯物主义的含义。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一百多年中,尽管对新唯物主义及其含义有多种不同的观点,但占据正统地位的始终是教科书理解模式的观点。然而它不仅没有能够正确把握新唯物主义及其含义,而且还严重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意,造成对新唯物主义含义长期深刻的误解。在当代中国,这种对新唯物主义含义的正统却不合理的理解仍然像一个沉重、坚固却无形的枷锁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说它沉重,是因为它的阻碍力和破坏力巨大,严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让人们无法动弹;说它坚固,是因为它让人们无法逃脱它的控制,要想破除更是困难;可为什么说它无形呢?这是因为虽然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然而人们却并没有明确意识到它的存在和危害。最具代表性的表现是,尽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新唯物主义的本质的主流观点发生了重大改变,由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转变为“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但是,即使这些发生了重要观念转变的学者也没有实现对新唯物主义含义理解的相应转变,仍旧对新唯物主义的含义持正统理解:世界的本体是物质,意识是派生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外部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自然界是优先存在的等。这里仅以几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本质有独立的和创新的理解的知名学者为例说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于新唯物主义含义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误解。
徐崇温先生提出,新唯物主义“要求……既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上,又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既把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独立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客观物质世界,又把它们看作是人的感性的活动的产物……之所以把它称作新唯物主义,是因为其内容的前一个方面,表明它和旧唯物主义一样,是一种哲学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7]“为什么仍然要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根本的原因在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8]“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都确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9]显然,在徐先生看来,和全部旧唯物主义一样,确认外部自然界、外部世界的优先地位始终是新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以十年艰辛的理论探索写成并提出了诸多重大新见解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中,张一兵先生这样写道:“马克思主要意在唯物主义地确证对象存在的客观性。”[10]大力提倡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王金福先生主张历史唯物主义“是包括物质本体论、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11]他还特别补充说明,“物质本体论也可以不是直观的唯物主义而是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12]无须多言,王先生仍然把物质本体论看作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和前提。和王金福先生相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的王东先生在其力作《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中同样把“自然存在前提论”当作包括新唯物主义在内的全部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
即使在这方面思想最为创新的辛敬良先生也依然保留了外部世界的物质性和客观性在新唯物主义中的前提地位。“不可否认,确认外部世界的物质性和客观性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但是将这一前提当作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就不恰当了。”[13]辛先生极具创造性地认为确认外部世界的物质性和客观性并不是新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这将对新唯物主义的理解大大向前推进了。但是,可以看出,辛先生所理解的新唯物主义仍然非常在意确认外部世界的物质性和客观性,仍然将其当作唯物主义包括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
“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重点……是在世界中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即物质和意识的地位问题。……马克思关注的究竟是物质占主导地位还是精神占主导地位……马克思的世界概念中当然包含了物质,物质当然是一切实践的前提;马克思的哲学不否认物质在时间上的先在性。”[14]显然,尽管王晓升先生对马克思哲学和新唯物主义的本质持同正统观点不同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但他也仍然以传统观点理解新唯物主义的含义。
以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对马克思新哲学和新唯物主义的本质都有各自新颖而独到的见解,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新哲学和新唯物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在新唯物主义的含义问题上,他们却全部没有走出传统观点的窠臼。这些知名学者对新唯物主义含义的理解代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新唯物主义含义的一般理解。
对新唯物主义含义没有真正理解使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逐渐发生改变的人们,不得不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的作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后面急忙补充道: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强调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主张外部世界不依赖于人、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坚持自然界是优先存在的。然而,事实上,如果把握了新唯物主义的真正含义,大可不必如此慌张,因为根本就没有必要做这样的补充和强调,这些根本就不是新唯物主义的含义,尽管马克思也的确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观点和自己的经验与理性认为自然界是先于人和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
质言之,尽管对新唯物主义本质的理解取得了重大进步甚至可以说实现了质的飞跃,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新唯物主义的含义却仍然被牢牢束缚在传统观点的思想藩篱之中而无法挣脱出来。与此不同,本书将努力把符合新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进行到底,让新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含义勇敢而明晰地呈现出来。
最后,不能准确、全面地理解新唯物主义的含义尤其是对新唯物主义含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在当代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理论乃至实践后果。在理论上,它阻碍了当代中国人对新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本质和精神的正确理解和把握,同时也阻碍了当代中国人对其他有价值的思想理论的正确理解和把握。在实践上,它助长了陈旧、保守的观念和态度,妨碍了当代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实践创新,阻碍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主义理论诞生一个半世纪之后的今天,重提新唯物主义的含义问题仍然是十分必要的。并且,我们或许还能以对这一问题的真正领会与阐释为基础和契机,更加有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