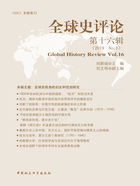
中国的国家政策、“经济发展”与性别
中国历史学家认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清代行政管理的一个特殊关注点,并且是一批被称为经世思想家的学者关注的焦点。[33]在中国,作为农民家庭收入辅助来源的纺织生产,在漫长的18世纪得到了扩展。长期以来,丝绸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对中国政府来说当然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为朝廷提供原料,而且在国内和国际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许多纺织工作是由男性织工在城市的专门作坊里完成的,丝绸生产的大部分阶段——至少是在纺丝线阶段——是以农户为基础的。在江南,农村家庭的主要纺织产品是缫丝以及捻或未捻的丝线。1700—1850年间,丝绸市场急剧增长。据李伯重估计,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生丝产量翻了一番多,从大约200万公斤增加到大约450万公斤,同时,用于种植桑树的农业用地比例翻了一番多(耕地从1.4%增加到3.3%)。与棉花相比,中国丝绸的生产主要是面向市场而不是家庭消费。[34]任以都声称,尽管丝绸市场在增长和变化,但是,以家庭和小作坊为基础的传统生产方式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35]
就像我们在欧洲所看到的那样,在中国清朝的国家战略中,有关工业技术和技能信息的散播也很重要。国家传播的信息中也包含关于丝织业工人的性别信息。为了配合其对鼓励发展经济感兴趣但又不能过多干预经济的做法,清政府推动代表理想农民家庭经济的教育资料的生产和流通。尽管还有其他国家编纂经济发展文献的例子,但是,我们还是从《耕织图》开始讲起。[36]17世纪末至18世纪,这些图被复制并作为木版画广为流传。清朝至少有三位皇帝将这些图作为官方文献颁印。[37]带有文本的木版被分发给地方官员,以便他们能够印发,该文本的非官方版本也广为流传。[38]这些画代表了农民生活的理想化愿景,它们清晰传达出这样一种观念,即合适的耕作(传统上被视为男性工作)和纺织(传统上被视为女性工作)技术对国家的福祉至关重要。当康熙皇帝颁印这些文本、想象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家时,妇女的纺织工作是这一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后世皇帝认可的一个构想。
清代的《耕织图》是根据早期一组同名绘画绘制的。正如我们所见,尽管关注人民福祉始终是儒家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一些话语在某些时代比在其他时代更重要。这种体裁在17世纪末重新流行起来,当时对国家非常有用。1689年,当康熙皇帝(1661—1722年在位)视察农业发达和文化先进的南方地区时,有人呈给他这幅作品的一份副本。恰逢其时地,这个文本又被重新引入国家政治话语,因为在当时争取汉人精英对新建立的满族政权的支持仍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在杭州,《耕织图》是作为记录南方习俗的一种方式被呈献给皇帝的。标题中的“耕”指的是水稻农业,这在北方并不普遍。因此,皇帝采用这份来自另一时空的文本,使它成为清初经济思想的标志性陈述。值得注意的是,康熙通过展示他对平民的仁慈关怀,明确地承袭了儒家统治者的衣钵。
当康熙回到北京后,他下令颁印了1696年的新版本。[39]该版本不仅收录了原作,而且连皇帝亲自创作的新诗也出现在了画作中。在正文的序言中,康熙皇帝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意图:“且欲令寰宇之内,皆敦崇本业,勤以俫之,俭以积之,衣食丰饶,以共跻于安和富寿之域。”[40]诗和插图既描绘了农业生产过程,也描绘了丝绸生产过程,生动地展现了几代人之间的家庭活动。耕图织图各23幅,每幅图都题有诗作,描绘了农民辛勤劳作的田园场景。1696年耕织图的木刻印刷版本流传广泛,有些版本是手工着色的,非常优雅;另一些则比较简单。这一举措在18世纪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它是朝廷提倡一种稳定社会的理想工具,这个稳定社会其基础是从事农业和养蚕业的合作无间的农户。当然,我们不能将这些图解读为真正实践的代表,但是,我们可以将它们解读为清朝流传的关于农户性别和代际分工的意识形态陈述——也就是说,作为政策想要实现目标的元层面框架。
在一幅“缫丝”图中(见图2),中心人物是一个妇女,她坐在一个大桶旁,另一个妇女在给她递蚕茧。但缫丝并不是这幅图中唯一的活动,还有个小孩在生火烧水;在院子的围墙处,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在与两个从墙外张望的孩子交谈。场景设置在围墙内的棚屋中,工作地点是在一个富裕的家内空间中,这表明缫丝的方式已嵌入其他性别化的家庭规则中。缫丝的工作似乎融入了这些妇女的日常生活,生产和生育成为并行的活动。

图2 《御制耕织图》
在地方和国家的资助下,这些画作的简略版得以传播。此外,在士绅的支持下,较为关注技术的新型画作开始出现。陕西有位士绅地主和学者杨屾(Yang Shen)就曾有过这样一个版本,他提供了一个更地方性的缫丝过程,成为官方以创业者角色干预丝织业的一个案例。杨屾在当地与陈宏谋(Chen Hongmou)共事,陈宏谋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清政府官员,他实际上在整个中国都推行经济发展运动,罗威廉认为,这些推动“把实现商业化既当作一个既定的目标,又当作一个企望的目标。陈宏谋在1740年代和1750年代在陕西推行的养蚕运动,也许是他所有推动经济的活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41]。中国的陕西省曾经生产过丝绸,但后来就不再生产了。对于一些地方士绅来说,恢复丝织业既可以重建当地昔日的荣耀,也可以维护当地的道德优势,与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如当时丝绸生产的龙头——位于东南部的江南地区)形成鲜明对比。杨屾在谈到养蚕业时,使用了罗威廉称之为“地方沙文主义者的措辞,这是在陈宏谋本人有关陕西丝绸生产的著述中很少见的”[42]。杨屾还主张在经济和道德上实行严格的性别分工;他的小册子中包含有工作时间表和插图(见图3和图4),图中显示了男女各自做的工作。

图3 纺织和缫丝,杨屾《豳风广义》

图4 提花机,杨屾《豳风广义》
虽然杨屾和陈宏谋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认为“小家庭生产模式无论从礼仪正统上还是经济效益上来看,都是最佳的模式”。杨屾从1725年开始在自家的土地上进行实验,在此基础上,中央和地方官员们萌生了重新引进丝绸的想法,并为杨屾建议、陈宏谋领导的为时13年的大规模实验奠定了基础,罗威廉将其视为一个“高度原创”的发展项目:
养蚕运动涉及丝绸生产过程不同阶段之间的方方面面,这些阶段包括:种植桑树、养蚕、缫丝、纺纱和织布。陈宏谋的一个关键性战略原则就是通过劳动分工,使每个人都能在丝绸生产过程的任何阶段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从而使尽可能多的农户参与进来。他还寻求建立一种激励机制,以吸引那些产量非常之少,以至于从事养蚕活动几乎无利可图的农户也能加入进来。他最终设计的体制非常类似于现在有时被称作“原始工业化”的体制,这种体制由中央实行控制,由地方组织,由高度分散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劳动者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供市场出售,这个市场至少有一部分是跨地区的。[43]
但与欧洲的原始工业相比,尤其是与18世纪普法尔茨为发展丝织业所做的努力相比,“原始工业化的主角不是商业资本家而是政府扮演的。虽然陈宏谋急切地想使植桑在陕西获得成功,但是,他坚持贯彻了两条基本经济原则,即自愿原则和市场激励”[44]。陈宏谋更多关心为所有人提供就业机会,而不太关心“传统的”性别分工,而像杨屾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和怀旧主义者,确实希望女性“回归”到男女分隔的工作中。陈宏谋对家庭生产的重视并不意味着除了家庭生产,他对政府建立养蚕作坊(“蚕馆”)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尤其是当他认识到,陕西当地生产者的技术水平相当低下。[45]尽管如此,陈宏谋把父权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设想,确实强化了传统的性别关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的发展计划却将纺织劳动力从家庭控制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丝绸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重点。1800年左右,越来越多的土地和劳动力被用于棉花生产。据李伯重估计,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江南的棉布产量翻了一番,从5000万匹增加到1亿匹左右。[46]当时,棉布已经取代了当地生产的麻布,同时,在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中国棉布也取代了印度棉布,并开始向西方出口。随着市场特别是出口市场产量的增加,一些产布地区农村妇女的工作重心似乎越来越集中在棉布的生产上,而她们的丈夫则越来越专注于农耕。李伯重声称,在纺织业产区,到18世纪末,妇女已完全放弃了农业劳动,而且“只有技术好、身体强健的妇女才能织布,而那些不太灵巧的老幼女性则只能用单个纱锭或更罕见的三个纱锭的纺纱机纺纱”[47]。
然而,正如我们在其他领域所看到的那样,尽管纺织业生产的经济意义越来越大,但清政府“较少干预国内商业经济的管理”。关于棉纺织业的商人或生产者组织,冯·格莱恩指出,“学者们的意见分歧主要在于商人控制棉花生产劳动过程的程度,但毫无疑问,许多农村家庭靠出售家庭手工艺品来满足他们的生存需要”。[48]曼素恩(Susan Mann)指出了清代商人组织的一些高度相关的职能,她提供的证据表明,这些职能似乎得到了国家的批准。她认为,商会不仅被赋予稳定价格和监管竞争的权力,还负责评估和征收商业税。有趣的是,曼素恩指出,地方士绅地主被从一些权力中排除。[49]这是我们发现的与欧洲国家最接近的类比,即国家权力委托给欧洲国家发展计划中起关键作用的商业公司。
欧洲某些地区的商业公司与政府合作发展原始工业,这使包括性别分工在内的农村经济格局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从短期来看,他们把工业引进农村地区,甚至给一些农村家庭带来了额外的收入机会。但是,他们的干预往往削弱了农业生存与工业发展相结合的可能性,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发生在爱尔兰,英国的亚麻政策导致了19世纪中叶的大饥荒。在其他地区,从19世纪初期到中期,危机以不同形式不断上演,但就像饥荒一样,把农民的子女赶出了农村——他们要么进入城市成为工业劳动力,要么漂洋过海成为美洲殖民者。
综上所述,我们关注1800年前后欧洲和中国不同国家经济政策对性别关系性质产生影响的比较证据。两者有一些相似之处,如国家对经济的各种干预,特别是对纺织业的干预,使国家与作为工农业生产基地的农村家庭的联系日益密切。即使农户仍在从事以自给为主的农业经济,国家政策也鼓励他们参与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国家采用多种方式,将与纺织品生产贸易有关的新财富来源合法化。通过所有这些机制,国家政策有助于改变家庭分工的决策,特别是年龄和性别分工。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无论是在欧洲国家之间,还是欧洲与中国之间,在家庭变革的性质和强度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到18世纪末,关于国家的新科学成为中欧和西欧大部分地区现代国家治理的标志。对经济、工业和人口的关注——事实上,将“经济”视为一个实体,视为国家规划、政策干预和与其他国家竞争的对象——是引入有效治理的一个关键方面。在经济学家的设想中,女性的家庭活动是与“经济”分开的,性别两极分化也越来越明显。欧洲政策的特点是“家庭劳动”与市场劳动的概念较早分离,但这只是强化了技术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要求纺织工人(通常是女性和年轻人)离开家庭去找“工作”——早在中国纺织工人遇到这种情况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尽管清政府的干预力度要小得多,但它强调保护以农业和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农户,这促成了性别分工的转变,但形式不同。曼素恩、李伯重等学者的研究指出,随着纺织业产区的增多,性别分工的分化更加明显。“清政府宣扬的思想有助于塑造晚清地方家庭社群的进取形象”,这些思想一再使家庭意识到“经济福利和社会地位与女性在家庭经济中的生产力息息相关”[50]。曼素恩进一步指出:“清朝统治者认为,家庭自给自足将成为农业经济快速商业化的主要障碍。”因为在这种模式下,鼓励家庭的衣食生产成为“经济发展”的一项主要策略,家庭的自给自足往往意味着妇女走出家门从事纺织工作,而男子则在田间劳作。[51]国家的统治思想还强调有必要帮助农民抵制城市和手工业的诱惑。我们可以把这种思维看作《耕织图》等史料中所体现的传统的男耕女织的性别模式。[52]
这与欧洲许多地区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洲统治者把经济发展的希望放在专业化、分工的加强和市场发展上(尽管工会确实为在中国并不存在的男性劳工特权提供了保障)。不过,这也表明,中国政府劝女性在家中从事劳动,这在19世纪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在19世纪末,第一批机械化的纺织厂开始引进中国,此时工厂主试图招募女工便遇到了困难。[53]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不太具有入侵性,这虽然有助于维护父权家庭的自主权,但也有助于解释19世纪国家的相对软弱。
(安·B.沃尔特纳 [Ann B.Waltner],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教授;玛丽·乔·梅恩斯 [Mary Jo Maynes],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教授;译者荆玲玲,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1] 还有很多文献对近代早期欧洲和中国的经济进行了对比,如刘芳《近代早期中国和欧洲的经济与国家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15年第1期;还可以参考以下学者的相关论文:舒建军、李伯重、刘景华、崔洪建、克雷格·穆尔德鲁(Craig Muldew)、李怀印、宋丙涛。
[2] Helen Dunstan,State or Merchant: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1740s China,Harvard East Asia Ser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6,p.468.
[3] Susan Mann,“Household Handicrafts and State Regulations in Qing Times”in Jane Kate Leonard and John Watt,To Achieve Security and Wealth:The Qing Imperial State and the Economy,1644-1911,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1992,p.78.
[4] Richard von Glah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From Antiquity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p.313.
[5] Helen Dunstan,State or Merchant: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1740s China,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No.273,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书评请参考 William T.Row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2,Issue 3,2007,p.828。
[6] Von Glah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pp.329-334.
[7] Helen Dunstan,State or Merchant: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1740s China,p.478.
[8] Helen Dunstan,State or Merchant: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1740s China,p.314.
[9] 引自Ravi Palat,The Making of an Indian Ocean World Economy,1250-1650:Princes,Paddy Fields,and Bazaars,New York:Palgrave,2015,p.8;Jürgen Kocka,Capitalism:A Short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p.42;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990-1990,Cambridge:Basil Blackwell,1990,pp.98-99。中译本见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公元990—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
[10] Ravi Palat,The Making of an Indian Ocean World Economy,pp.7-8.李怀印有相似的看法,他认为,战争对欧洲国家建构的影响比中国清朝更为强烈,见Li Huaiyin,“Fiscal Cycles and Low-Level Equilibrium under the Qing:A Comparative Analysis”,Social Sciences in China,No.1,2015,pp.144-171。
[11] Von Glah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pp.345-346.
[12] Von Glah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p.315.
[13] Jürgen Kocka,Capitalism:A Short History,pp.50-51.
[14] 这里使用的词是“招商”。
[15] Sun,E-tu Zen,“The Finance Ministry(Hubu)and Its Relation to the Private Economy in Qing Times”,in Jane Kate Leonard and John Watt,To Achieve Security and Wealth:The Qing Imperial State and the Economy,1644-1911,1992.
[16] William Rowe,Saving the World: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98-201.中译本见罗威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陈乃宣、李兴华、胡玲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7—290页。
[17] Von Glah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p.304.
[18] Marion Gray,Productive Men,Reproductive Women:The Agrarian Household and the Emergence of Separate Spheres during the German Enlightenment,New York and Oxford:Berghan Books,2000.
[19] Marion Gray,Productive Men,Reproductive Women:The Agrarian Household and the Emergence of Separate Spheres during the German Enlightenment,New York and Oxford:Berghan Books,2000.
[20] Robert S.DuPlessis,The Material Atlantic:Clothing,Commerce,and Colonization in the Atlantic World,1650-18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21] Thomas Prior,An Essay to Encourage and Extend the Linen-Manufacture in Ireland by Praemium and other Means,Dublin,1749,pp.4-5.
[22] Thomas Prior,An Essay to Encourage and Extend the Linen-Manufacture in Ireland by Praemium and other Means,pp.26-27.他还写道:“穷人起初可能买不起纺纱机或亚麻来干活,在这种情况下,地主给他们提供纺纱机和亚麻是合适的,因为这样一来,纺纱工就可以用他们的纱线获得的利润来偿还。”
[23] Carmen Sarasúa,“Technical innovations at the service of cheaper labour in pre-industrial Europe:The Enlightened Agenda to Transform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ur in Silk Manufacturing”,paper at the XIV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Helsinki,Finland,p.22.
[24] Christophe Isnard,Mémoires et instructions pour le plant des meuriers blancs,nourriture des vers à soye,et l'art de filer,mouliner et aprester les soyes dans Paris et lieux circonvoisins,Paris,1665.
[25] Carmen Sarasúa,“Technical innovations at the service of cheaper labour in pre-industrial Europe”,p.1.
[26] François-Félix de La Farelle,Études économiques sur l'industrie de la soie dans le Midi de la France,Paris:Guillaumin,1852-1854,premier etude,pp.4-5.
[27] Du Perron,“Observations intéressantes adressées à MM.les syndics et maîtres-gardes des manufactures en soie,sur la nécessité d'un règlement”,1773.
[28] Isbard,243.
[29] La Farelle,Études économiques sur l'industrie de la soie dans le Midi de la France,second etude,p.2.
[30] Carmen Sarasúa,“Technical innovations at the service of cheaper labour in pre-industrial Europe”,p.11.
[31] Bernhard Scheifele,“Seidenbau und Seidenundustrie der Kurpfalz”,in Neue Heidelberger Jahrbücher16,1910,pp.193-256.
[32] Bernhard Scheifele,“Seidenbau und Seidenundustrie”,pp.240-247.
[33] 关于经世思想家的著作可参考Susan Mann,“Household Handicrafts and State Regulations in Qing Times”,1827年出版的《皇朝经世文编》中也有记载。
[34] Li Bozhong,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pp.33,34,92.
[35] E-tu Zen Sun,“Sericulture and Silk Textile Production in Ch'ing China”,in William E.Willmott,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p.79-108.
[36] 如,曼素恩在其文章中曾讨论过几个国家授权的描述或鼓励棉花生产技术的蓝本,具体内容请参考Susan Mann,“Household Handicrafts and State Regulations in Qing Times”。
[37] 首先是康熙,其次是雍正,最后是乾隆。
[38] Peter Golas,Picturing Technology in China: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Ninteenth Century,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5,p.150;Francesca Bray,“Agricultural Illustrations:Blueprint or Icon?”,in Graphics and Text in the Production of Technical Knowledge in China,Leiden:Brill,2007,p.530.
[39] Marcia Reed and Paola Dematte(eds.),China on Paper:European and Chinese Works from the Late Sixteenth to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96.
[40] 康熙:《耕织图序》,张廷玉:《皇清文颖》,卷首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 William Rowe,Saving the World: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p.235.
[42] William Rowe,Saving the World: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p.236.
[43] William Rowe,Saving the World: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p.237.
[44] William Rowe,Saving the World: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pp.237-239.
[45] William Rowe,Saving the World: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pp.240-242.
[46] Li Bozhong,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p.34.
[47] Li Bozhong,“Involution and Chinese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Songjiang in the Late-Eighteenth and Early-Nineteenth Centuries”,in Giorgio Riello and Prasannan Parthasarath(eds.),The Spinning World:A Global History of Cotton Textiles,1200-185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90;Kenneth Pomeranz,“Women's Work,Family,and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East Asia:Long Term Trajectories and Contemporary Comparisons”,in Giovanni Arrighi,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New York:Routledge,2003.
[48] Von Glah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pp.298-316.
[49] Susan Mann,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1750-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23-24.
[50] Susan Mann,“Household Handicrafts and State Regulations in Qing Times”,pp.75-76.
[51] Susan Mann,“Household Handicrafts and State Regulations in Qing Times”,p.76.
[52] Susan Mann,“Household Handicrafts and State Regulations in Qing Times”,pp.79-80.
[53] Susan Mann,“Household Handicrafts and State Regulations in Qing Times”,pp.9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