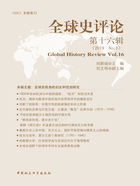
关于文明的政治地理学与性别的特定影响的争论:天下、欧洲国际社会和妇女作为社会政治能动者的出现
西方势力发起和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国于19世纪被纳入其中)存在着不同的互动模式,这些互动模式决定了欧洲国家之间以及欧洲国家与非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旨在“容忍与共存”,而非欧洲国家是按照“文明标准”来衡量的。讨论国际社会时,铃木写道:
……在19世纪晚期,中国和日本交锋并被纳入国际社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坚信欧洲“文明”的优越性,并由此认为欧洲国家有义务用武力传播欧洲文明的福音,必要时也可直接殖民。由此,与“野蛮”的非欧洲国家的互动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扩张主义特征。[17]
当谈到“文明”一词的含义时,铃木认为文明的具体标志物就是遵从国际法和欧式外交制度,这使得某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处境得以合法化。然而,赖骏楠(Junan Lai)对19世纪西方法学史进行了探究,认为“文明”一词的内涵并没有明确的界定。[18]与此同时,其他学科的学者对冷战前近代史上“文明”标准的探索,提供了更为复杂的视角。[19]他们认为,妇女的处境,她们的身体、思想、愿望和活动与其他具体标志物一起构成和展示着西方文明。
晚清中国不需要按照文明和野蛮这一区分引入对世界秩序的确立。“天下”——中国人定义的以皇帝(天子)为辐射中心的文化和文明的世界[20]——就有相似的文明矩阵,并延伸为政权分配形式。
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这样描述前近代中华帝国以文明为中心的区划观念:
这个统治者处于等级结构中心的模式……将世界划分成一系列等级和教化递减的空间区域。首先是统治者所在地区,也就是都城地区,其次是封建领主控制的地区,然后是被当朝占领或平定的地区,最后是蛮族统治下的地区。[21]
“天下”,或陆威仪所说的“世界帝国”,是靠朝贡体系这种制度来维系的,作为贯穿于礼治、政治和文化的“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朝贡体系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联系在一起。[22]儒家思想/新儒家思想不断变化,经久不衰,是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混合体,与中国的自我认知、政治体制和世界秩序密切相关。中国人以儒家/新儒家思想为支撑,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对自己的标准、习惯和价值观引以为豪,声称中华文明具有无可争议的文化优势。[23]换句话说,就像19世纪侵犯中国的那些帝国一样,前近代中国想象并管理天下,制定与异邦往来的行为准则,并且“作为地区霸权……在世界秩序中享有规范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24]。
在“天下”世界的秩序中,中心和边缘有严格的区分,具体来说就是从中心辐射出一系列逐渐远离中心的同心区域,其在秩序中的重要性逐级递减;由此,政治权力的地缘文明空间“按照‘内’(内部)高于 ‘外’(外部)的原则”被用来划分等级。[25]作为一个二元术语,“内—外”主要是内外部边界的空间标记,内部代表朝廷统辖的有序的文治区域,而外部代表与朝廷对抗的混乱的军事区域。将“内”部的汉文明状态与“外”部未开化的无序状态区分开来的是恰当的礼仪,而礼仪又是通过掌握“礼”(恰当礼节)和施行“别”(性别化分)来界定和施行的。[26]在这些观念中,仪式化的性别角色被视为中国文明优越性的组成部分。以这些观念为基础,当提及中华帝国统治和文明优越性时,中国妇女——我们讨论和规定的妇女,而并非真正的妇女和她们的实际生活——被置于中心位置。
一些学者论证,在中华帝国文明版图确立的过程中,以及在文化霸权自我形象的塑造中,中国文人是如何将儒家/新儒家汉族女性定位为“天下”世界的文明尺度的。他们的研究表明,女性之所以成为前近代中华文明的标志,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新儒家女性教育、缠足和女性劳动。[27]就此,高彦颐(Dorothy Ko)在她关于缠足的讨论中提到一个最直接的例子,说明在中国对妇女的文化和政治诠释和对中华文明的自我认知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以及前者是如何塑造后者的。高彦颐写到,在中国诱化其俗的过程中,中华帝国外围非教化地区及其居民可以被纳入中华文明世界,途径为构建当地历史,成立儒学学校,以及追封有德行的女性。[28]高彦颐进一步指出,在教化蛮族地区和蛮族的设想中,缠足被界定为“有道德的中国女性必备的‘服装’”和“中国所垄断的文明的标志”[29]。
19世纪下半叶,在与外国势力的战争中,中国均以失败告终。即使我们将1840年以来强加给中国的条约理解为“对清朝的策略,以接纳西方国家,并在中国范围内给他们安排位置”,[30]但事实是,自1874—1895年,法国开始控制越南,日本接管控制琉球群岛和朝鲜,中国失去了对“三个最重要的朝贡国的控制”[31]。从而,1895年的《马关条约》“……不仅象征着中国彻底的军事失败,也终结了中国仅存的与朝鲜的朝贡关系,这标志着东亚国际秩序的最终崩溃。此后,中国别无选择,只能更全面地参与欧洲国际社会”[32]。
在19世纪下半叶意识形态激烈冲撞的时期,与性别相关的文明标志的含义是颠倒的:女性原本被视为中华文明优越性不可或缺的因素,如今却被诟病为愚昧无知、肢体残疾、是中国孱弱和耻辱的分利原因。[33]焦虑的中国男性文人试图将中国从政治和文明的半边缘地带拉回到中心位置,他们宏伟计划的一部分就是改变中国女性——中国女性长久以来就是中国文明统治和成就的标志。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女性被看作衡量世界秩序的(用安·唐斯的话来说)“一根标尺”[34]并非始于19世纪。19世纪的历史意义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由新的进化宇宙论[35]所带来的“巨变的意义结构”之应对,不仅动摇了中国作为文明的唯一来源的自我形象,而且引发了对文明的重新思考。换句话说,一个关键问题是,在相似的西方文明的地缘政治权力分布矩阵中,其妇女和文明的关系也很相似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引进和宣扬了对于文明的不同理解,他们将中国定位为半文明半殖民地国际社会成员,并给予相应待遇。
由于男性改革派主张女性改革应该成立新组织和学习新内容,并使用前所未有的新途径,中国一些面向女性的项目便邀请了改革者所宣传的对社会干预很有经验的外国人参与其中。最初,一个支持女性改良事业的男性网络建立起来,这个网络包括中外教育家、官员、传教士、外交官、实业家、企业家以及出版界的知名人士。[36]然而,新儒家的礼制反对男性无限制地接近女性,这就需要西方女性参与改革计划。于是,中国的男性改革者要求他们的外国合作者提供“一份对‘改革’计划特别感兴趣的在沪外国女性名单”[37]。一些“外国女性”确实被介绍给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改革者的女性亲戚和熟人,最早的中国妇女社团“女学会”、第一个中国人自办的女子学校“女学堂”和妇女报纸《女学报》也在创建中。[38]本文的下一部分将认真审视中国女性如何看待权力的不断重构和意义的现代化转变,并对她们重构的世界秩序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