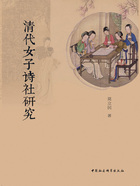
第一章 清代女子诗社兴盛的历史传统、时代语境与组织结构
第一节 历史传统与时代语境
一 历史传统
我国古代文人很早就有诗文雅会的历史传统。虽然此期的诗文雅会还谈不上是诗词结社活动,但或多或少均带有文人结社的质素,并最终为后世文人和闺秀诗词结社树立起足以模仿与景仰的典范。见诸文献的我国古代文人最早的诗文雅集活动是被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西汉早期的“梁园雅集”。“梁园雅集”是指西汉汉景帝时期以梁孝王刘武、著名文士司马相如二人为中心而形成的文学群体创作活动。梁孝王广筑苑囿,延揽天下俊杰与文士,一时文学英才如司马相如、枚乘、邹阳、严忌等人纷纷就养于梁园,他们朝夕相处,研习辞赋,形成我国文学史上最早且影响颇为深远的文学创作群体。顾况《宋州刺史厅壁记》云:“梁孝王时,四方游士邹生、枚叟、相如之徒,朝夕晏处,更唱迭和。天寒水冻,酒作诗滴,是有文雅之台,清泠之地,雁鹜之所栖集,园苑三百余里。”[1]
到了西晋,石崇等人的“金谷宴游”,则既是政客们的政治交结行为,也是文士们有意义的诗歌雅集活动。石崇《金谷诗序》记载:“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2]
东晋王羲之的“兰亭修禊”,被中国古代文士们视为千古佳话。东晋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初三,王羲之与当朝官宦及著名文士谢安、孙绰等41人,依据民间于此日到水边沐浴、洗濯,借以除灾去邪的“修禊”习俗,相约来到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市)的兰亭水边,一面作流觞曲水之戏,一面喝酒赋诗,众人将即兴写成的诗歌编成诗集《兰亭集》,王羲之为之作序,千古不朽的《兰亭集序》就这样横空出世了。王羲之《兰亭集序》这样记载这次文人雅集的“修禊”活动:“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3]
其后,文人诗酒雅集唱和活动蔚为风气,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一种颇值得关注的文化与文学现象。《南史·顾越》本传:“承圣二年(553),诏授宣惠晋安王府谘议参军、领国子博士。越(顾越)以世路未平,无心仕进,因归乡,栖隐于武丘山,与吴兴沈炯,同郡张种,会稽孔奂等,每为文会。”[4]《南史·徐伯阳》本传:“太建初,与中记室李爽、记室张正见、左户郎贺彻、学士阮卓、黄门郎萧诠、三公郎王由礼、处士马枢、记室祖孙登、比部郎贺循、长史刘删等为文会友,后有蔡凝、刘助、陈暄、孔范亦预焉,皆一时士也。游宴赋诗,动成卷轴。伯阳为其集序,盛传于世。”[5]
两晋南北朝,不仅在官僚、文士之间流行诗酒雅会,而且随着佛教等外域宗教流播中土,以传佛、奉佛为宗旨的群体结社也开始出现。东晋名僧慧远在庐山所结的白莲社,即为此期崛起的著名宗教社团。《庐山记》记载:“谢灵运恃才傲物,少所推重,一见远公,肃然心服,乃即寺翻《涅盘经》,因凿池为台,植白莲池中,名其台曰翻经台,今白莲亭即其故地。远公与慧永、慧持、昙顺、昙恒、竺道生、慧睿、道敬、道昺、昙诜、白衣、张野、宗炳、刘遗民、张诠、周续之、雷次宗、梵僧佛驮耶舍、佛驮跋陀罗,十八人者,同修净土之法,因号白莲社。”[6]又《佛祖通载》:“时晋室微,而天下奇才多隐居不仕。若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士民、李硕等,从远游,并沙门千余人结白莲社。于无量寿像前,建斋立誓,期生净土”[7]。白莲社是一个聚合文士与僧人,且以传佛、奉佛为宗旨的社会群体,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早见诸文献记载的有正式社名的文人社团。
有意思的是,此期不仅有诸多高级或中层文士参与或主持宗教结社活动,也有众多的社会庶民及女性加入这一社会活动之中。留存至今的北朝东魏武定三年(545)写成的《邑义造迦叶像记》简略记载了其时女性结社奉佛的情况:“大魏武定三年,岁在乙丑五月己卯八日丙戌,郑清合邑义六十人等,敬造迦叶石像一躯。上为皇帝陛下,臣僚伯(百)官,州郡令长,师僧父母,因缘眷属,普及法界众生,有形之类,一时成佛。奇哉邑母,识知无常,缘乡劝花(化),造石金刚,舍此秽形,早登天堂。合邑诸母,善根宿殖。昼夜忧惶,造像永讹,释迦已过,弥勒愿值。”[8]在两晋南北朝,为弘扬佛法所结成的佛社通常被称为邑、邑义、邑会、法义等,文中将邑义成员,即佛社中的成员称为“奇哉邑母”“合邑诸母”,显然,文中的这个“邑义”主要由成为母辈的中老年妇女组成。
延及隋唐五代,文士诗酒雅会之风与社会上宗教结社之习较之两晋南北朝更为兴盛。盛唐著名诗人孟浩然《宴张记室宅》诗云:“甲第金张馆,门庭车骑多。家封汉阳郡,文会楚材过。曲岛浮觞酌,前山入咏歌。妓堂花映发,书阁柳逶迤。”《旧唐书·吴筠》本传云:“筠尤善著述,在剡与越中文士为诗酒之会,所著歌篇,传于京师。”[9]文士与僧人所结之佛社在此期也不时出现在文籍中。唐代诗人皇甫冉诗云:“东林初结社,已有晚钟声。”[10]又陈羽诗:“天竺沙门洛下逢,请为同社笑相容。”[11]张登诗:“招取遗民赴僧社,竹堂分坐静看心。”[12]这些唐五代作家的著述均为纪实之作,真实状写出隋唐五代时期文士诗酒雅会之盛与社会上宗教结社之隆。
传承南北朝以来妇女礼佛结社的传统,唐五代妇女宗教结社不绝如缕,但在功能与作用上则有诸多变化。南北朝的女人社以礼佛奉佛为宗旨,唐五代女人社虽仍然有礼佛奉佛的作用,但它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世俗生活,颇多结义互助的元素。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女人社社条》云:“夫邑仪(义)者,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值;危则相扶,难则相救;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者若姊,小者若妹,让语先登。”[13]
值得注意的是,唐五代时期还零零星星地出现了以“诗社”“吟社”命名的文人诗歌结社活动。如初唐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著名诗人杜审言即在江西吉州(今江西吉安)结“相山诗社”,中唐著名诗人戴叔伦也曾结社吟诗,其《卧病》诗云:“门掩清山卧,莓苔积雨深。病多知药性,客久见人心。众鸟趋林健,孤蝉抱叶吟。沧洲诗社散,无梦盍朋簪。”[14]晚唐藩镇大吏高骈政事之余,曾经结社赋诗,其《途次内黄马病寄僧舍呈诸友人》诗曰:“好与高阳结吟社,况无名迹达珠旒。”[15]此外,五代著名诗人廖融也曾组织过诗社。《西江诗话》:“廖融,字元素,虔化人(今江西宁都县)。唐末隐南岳,与逸人任鹄、凌蟾、王正已、王元共结吟社。自号衡山居士。”[16]
逮至两宋,不仅文人文学与宗教结社风习一路向上,蓬勃兴盛,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社会各行各业也大兴结社之风,形成我国古代结社运动第一波高潮。歌舞行业方面:“姑以舞队言之,如清音、遏云、掉刀、鲍老、胡女、刘衮、乔三教、乔迎酒、乔亲事、焦锤架儿、仕女、杵歌、诸国朝、竹马儿、村田乐、神鬼、十斋郎各社,不下数十。更有乔宅眷、旱龙船、踢灯、鲍老、驼象社。”[17]饮食行业方面:“次八仙道人、诸行社队,如鱼儿活担、糖糕、面食、诸般市食、车架、异桧奇松、赌钱行、渔父、出猎、台阁等社。”[18]耐得翁《都城纪胜》“社会”条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南宋时期民间社会结社之风的兴盛:“又有蹴鞠打球社、川弩射弓社。奉佛则有上天竺寺光明会,皆城内外富家助备香花灯烛,斋衬施利,以备本寺一岁之用。又有茶汤会,此会每遇诸山寺院作斋会,则往彼以茶汤助缘,供应会中善人。城中太平兴国传法寺净业会,每月十七日则集男士,十八日则集女人,入寺讽经听法。岁终则建药师会七昼夜。西湖每岁四月放生会,其余诸寺经会各有方所日分。每岁行都神祠诞辰迎献,则有酒行。锦体社、八仙社、渔父习闲社、神鬼社、小女童像生叫声社、遏云社、奇巧饮食社、花果社;七宝考古社,皆中外奇珍异货;马社,豪贵绯绿;清乐社,此社风流最胜。”[19]
在社会各界争相结社的社会风尚的影响下,宋代诗社云蒸霞蔚,群出林立。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考证出宋元诗社60多家,陈小辉博士学位论文《宋代诗社研究》统计出北宋诗社93家,南宋诗社144家,共得两宋诗社237家。其中北宋文彦博洛阳耆英会、贺铸彭城诗社、邹浩颍川诗社、徐俯豫章诗社、叶梦得许昌诗社、南宋王十朋楚东诗社、辛弃疾铅山诗社、杨万里吉州诗社、范成大新安诗社、陆游临安诗社、周紫芝无为诗社等,均为两宋时期有较大影响且社群质素成熟的著名诗社。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曾对两宋时期诗社之盛的主要原因有精辟论述:“宋代诗社的兴盛,与当时皇帝的倡导不无关系。在宋代,皇帝专设赏花钓鱼宴,其制为‘三馆直馆预坐,校理而下赋诗而退’。这种赏花钓鱼宴,有时又称‘赏花钓鱼会’。同时,宋代士大夫的聚会之风也颇盛,对诗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
明代继宋元之后,社会上三教九流结社之风朝气蓬勃,蒸蒸日上,两宋以来掀起的结社风潮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深化。明代各行各业均有自己的会所,行商有商会,科考有文会,习武有武行,各种会所纷至沓来,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而文人文学与政治结社活动则一浪高过一浪,在明末清初达到最高值,形成我国古代文人结社运动的最高峰。当代学者李时人指出:“至有明一代,‘文人结社’则达到空前的兴盛。20世纪40年代,郭绍虞作《明代的文人结社年表》一文,辑考出‘明代文人结社’达176家。2003年,何宗美在《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中提出明代‘文人结社’已‘超过三百例’,至其2011年出版的《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又稽考出‘明代文人结社的个案’(含元末)680余家。李玉栓2006年至2009年从我攻读博士学位,所撰论文《明代文人结社考》在前哲时贤的研究基础上,大量翻检明人诗文集、明人年谱、地方志乘以及相关的史料、笔记、杂传、墓铭等各类文献资料,共考得明代(不含元末、含南明)‘文人结社’530多家,毕业后又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最终增补至710家,另有社事时间难以确知的220家作为附表列于书后,凡得930家。而据其所言,‘明代文人结社’的总量实际应当在千数以上。”他又指出:“除了数量,明代‘文人结社’的种类也很繁多。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考》将其大略分为‘研文类结社’、‘赋诗类结社’、‘宗教类结社’、‘怡老类结社’、‘讲学类结社’和‘其他类结社’,而最末一类所含甚广。至于明代各种结社体制之完整、规模之巨、活动内容之丰富、延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也都超过往古。”[21]
中国古代女子诗社出现较迟。现在能考出的中国古代最早的女子诗社是明末安徽桐城方氏闺秀“名媛诗社”。这个诗社以桐城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三姐妹为核心。但中国古代女性结社历史却源远流长,起码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女性宗教结社。延及隋唐五代,女性结社范围又从宗教结社扩展到世俗生活结社。中国古代女子诗歌结社在明末清初这个历史节点得以爆发,但这个爆发点的引爆时间却经历了两汉至元明近两千年的酝酿、准备期。
固然,清代女子诗社的兴盛有其渊源有自的历史传统。一方面,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文人文学雅集与社会各界群体结社活动为清代女子诗歌结社挹注出丰富的诗歌创作与社会群体活动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也为清代女子诗歌结社培植出厚实而多样态的诗歌创作与社会群体运动的文化基础。尽管清代女子诗社得以全面繁荣的原因诸多,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文学本体发展等多力合成的结果,但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文人文学雅集与社会各界群体结社活动却是其茁壮成长的历史根基。
二 时代语境
“语境”,即语言环境,原本是语言学学术概念之一,主要指语言表达上下文、语言表达情景与对象、语言表达前提等与语词使用有关的语言表达的具体环境。它既有语言因素,也涵括非语言因素。黄伯荣、廖序东这样解释“语境”的语言学含义:“语境就是语言单位出现时的环境。一般分为上下文语境和情景语境(又叫社会现实语境)。”[22]后来,“语境”一词被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所借用,并衍生出与相关学科有紧密联系的语义、语用与语义场。此处所说的“时代语境”,侧重于历史学与文化学的语义、语用与语义场,主要指促成、催生清代女子诗社得以生成并最终走向兴盛的具体社会、文化环境。
中国古代女子诗社之所以开启于晚明,兴盛于清代,与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时代语境”,即与这两个时代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
时代语境之一:中晚明时期思想钳制渐次松弛,商品经济逐步发展并繁荣,形成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思想与社会形态均紊杂而开放的时期。
明朝初期,开国太祖朱元璋与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均大力推行传统礼法,尽力恢复并重构传统宗法体系与社会秩序,彼时一方面思想管控严密,社会缺乏自由,另一方面却也民风淳朴,士风惟谨。
明初洪武年间,朱元璋在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基础上,刻意强调重农抑商的思想。“(洪武)十四年令农衣䌷、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䌷、纱。”[23]政府还强力推行科举制,给予读书士子物质和精神上的优厚待遇,大力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由此,非惟商贾阶层不惜重金延师教子,以期改换门楣,就是“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教子孙读书为事”[24]。
明朝初年政府还对社会各等级的服饰、住宅等生活细节进行具体规划:“洪武三年,庶人初戴四带巾,改四方平定巾,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又令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止许䌷、绢、素纱,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止用银。六年,令庶人巾环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未入流品者同。庶人帽,不得用顶,帽珠止许水晶、香木。”[25]还规定:“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栱,及绘藻井,惟楼居重檐不禁。公侯,前厅七间、两厦,九架。中堂七间,九架。后堂七间,七架。门三间,五架,用金漆及兽面锡环。家庙三间,五架。覆以黑板瓦,脊用花样瓦兽,梁、栋、斗栱、檐桷彩绘饰。门窗、枋柱金漆饰。廊、庑、庖、库从屋,不得过五间,七架。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栱、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五架,绿油,兽面锡环。三品至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三架,黑油,锡环。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梁、栋饰以土黄。门一间,三架,黑门,铁环。品官房舍,门窗、户牖不得用丹漆。功臣宅舍之后,留空地十丈,左右皆五丈。不许挪移军民居止,更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以资游眺。”[26]
在明初政府的强力介入下,明初社会生活俭朴,市井风气也比较淳朴。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记载明初社会生活状态时说:“其便服自职官大僚而下至于生员,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绸、纱绫、缎道袍,其华而雅重者,冬用大绒茧绸,夏用细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朴素者,冬用紫花细布或白布为袍,隶人不敢拟也。”又说:“其市井富民,亦有服纱绸绫罗者,然色必青黑,不敢从新艳也。”[27]
然而,到了嘉靖之后的中晚明,明朝统治者对意识形态的管控渐次松懈,明朝社会思想与经济发展逐步多元化,明人的人生价值取向、生活消费观以及具体的生活方式较之明初发生了重大改变。
中晚明时,皇帝怠政、荒政成为一种常态。嘉靖帝晚年迷信神仙之道,持续多年疏离朝政;万历皇帝则有20多年不上朝,明廷运转几乎停摆。万历十七年(1579)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曾上奏疏骂神宗皇帝:“皇上之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又说:“皇上诚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会?皇上诚恋色矣,何以禁臣下之淫荡?皇上诚贪财矣,何以惩臣下之饕餮?皇上诚尚气矣,何以劝臣下之和衷?”[28]
与此同时,商品经济开始逐步发展并在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土地兼并与其他产业的兴起,明中叶以后,许多农民弃农而改工商,商品经济方兴未艾。明人何良俊记载苏、松一带商品经济发展时说:“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闲者(城市临时觅工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29]
与政治松动和经济多元同步的是,中晚明时期传统儒家宗法礼教也受到冲击,个性与物质主义在社会各阶层中广受欢迎并成为时代的思想主潮。晚明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就公开倡言物质与享乐主义,他说:“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叫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30]袁宏道之弟袁中道在一首小诗中宣称:“人生贵适意,胡乃自局促。欢娱极欢娱,声色穷情欲。”[31]晚明文人张岱则公开表白自己有“十二好”:“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32]
中晚明时代社会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变化有其消极因素,它助长了人们的身体享受欲与物质占有欲,也必然加剧明廷统治者的腐化以及社会弊端的滋长。另外,它又打破了明代前期沉闷、拘谨的社会体系与社会风气,令中晚明社会有了开放与多元的元素,多了几许“活力”与“生动”,一些人性的健康基因与未来社会的正向构建结构在此得以成长,产生出一些“新概念”与“新名词”,而中晚明女性也由此获得较之明初更多的人生与社会自由。
时代语境之二:女性文化教育与才女文化被社会广泛接受,成为中晚明与清代的一种社会风尚。
中国古代女性教育源远流长。先秦时代贵族家庭就任用“傅母”来看护、教育自己的子女。《穀梁传·襄公三十年》:“伯姬曰:妇人之义,傅母不在,宵不下堂。”[33]《汉书·张敞传》:“礼,君母出门则乘辎,下堂则从傅母。”[34]至于一般平民家庭的女性,也有自己的人生职责与学习任务。《礼记·内则》:“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35]总体来说,先秦时代的女性教育虽有文化知识元素,但主要是一种生存技能与人性道德教育,其主要目的是要培养出能吃苦耐劳、善于治家的优秀女性。
从两汉到元代,女性的文化教育仍然得到部分家庭的重视,如东汉大学者蔡邕就很重视对女儿蔡文姬的文化培养,他给女儿“赐书四千许卷”[36],唐代著名的宋若昭、宋若伦等“宋氏五姊妹”也因其父“(宋)庭芬始教以经艺,既而课为诗赋,年未及笄,皆能属文”[37],然而,两汉至宋元的社会整体教育氛围依然沿着先秦时代的女性教育路径前行,十分重视女性的生存技能与人性道德教育,并且逐步强化。如东汉班昭撰写《女诫》,就强调女性的“卑弱”地位。她在《卑弱第一》中指出:“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齐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38]又在《敬顺第三》中说:“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女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39]唐代宋若莘著《女论语》,对女性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均做具体规定,力图使每一位女性都成为既勤劳又品德高尚的人:
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身之法,惟务清贞。清则贞洁,贞则身荣。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行。男非眷属,莫与通名,女非善淑,莫与相亲。立身端正,方可为人。[40]
中国古代女性文化教育真正得到社会广泛承认,并形成一种社会潮流,则始于明代中后期。晚明文学家葛征奇在谈到明代女子文教兴盛的盛况时曾说:“国朝以文明御宇,里歌巷诵,渐被士女。历三百年间,名媛闺彦,项背相望,自江南北以及吴、越、鲁、蜀,声播金石,为一代鼓吹,猗与盛哉!”[41]清人丁绍仪也曾论及清代女子的文教之盛:“吴越女子多读书识字,女红之暇,不乏篇章。近则到处皆然,故闺秀之盛,度越千古。”[42]具体而言,明清时期女性文教之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明清两朝女子文化教育广泛而普及。
其一,明代,尤其是中晚明,由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与社会风气的开放,女子文化教育已被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他们通过种种努力,让自己家庭内的女性获取一定的文化知识。明初著名女诗人朱妙端,“幼颖悟,得其家学,以诗鸣于时”[43]。晚明女诗人张引元“六岁能诵唐诗三体,皆得母王文如之训”[44]。清代众多家庭对女性文化教育的重视与明代比照并不逊色。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就记载了不少女性接受文化教育的事例。如吴丝、顾慈、吴婉宜等人自小就由父亲开蒙识字,对她们进行诗词教育。丁瑜、万藻、顾兆兰、马荃等人也得父家传,擅长画画或书法。而闺阁女子朱淑均“受诗法于祖,受画法于叔”[45]。
明清两朝,许多有条件的家庭,不仅父母等亲属传授知识给女性,还会请闺塾师来教家中女孩识字读书。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女官传》中记载明初宫廷女官陈二妹所受文化教育时说:“七岁就女师,闻爱亲敬长之言,必反复致问,《孝经》、《内则》、《列女传》、《女诫》诸书,莫不潜心究之。”[46]汤显祖《牡丹亭·闺塾》就生动描绘出明代女子“师授”教育的基本情况。塾师陈最良一开口就说:“我陈最良杜衙设帐,杜小姐家传《毛诗》。”还讲到了他教学的具体内容:“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姜源产哇;不嫉妒,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皋》,思《汉广》,洗尽铅华,有风有化,宜其室家。”[47]到了清代,这种延师授教闺中女性的社会风尚仍然得到继承与发展。日本学者中川忠英曾这样描述清代女性延师授教的情况:
女子上学之法与男子亦无不同,但均由才学之寡妇或良家妻女作为女先生,每日来到各家,教授各家女子。开始时教《女诫》、《孝经》,然后再和男子同样使读《千字文》、《百家姓》、四书等书文。贽仪、束脩之礼亦与男学生同。[48]
其二,明代以前,女子文化教育多“学在上层”,大多局限于贵族和中上层知识精英阶层内。明清两朝女性文化教育的范围则大大扩大,不仅政治与经济优越的女性文化教育大多得到保证,就是一些平民或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有时也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清中叶李调元对清代女性教育范围的扩大曾有描述:“武林(今杭州)女媛多能诗,不但朱门华胄,即里巷贫户能诗者亦复不少。”[49]清代著名词人吴藻“父夫俱业贾,两家无一读书者”,但她则“喜读词曲”[50];吴江女子汪玉轸,“父兄夫婿,皆非士人”[51],她却工诗善书,成为小有成就的才女。雷瑨、雷瑊《闺秀诗话》记载:“扬州西乡有农家女者,年方十五,为巨室某姓家婢。某夫人能诗,见其颖慧,辄教以吟咏,不三年而成,里中辄以才女目之。”[52]清人王倬《课婢约》则写道:“有婢初来,年方十四,指挥未谙,约法数章。翰墨图书,只此是吾长物,牙签玉轴,从令隶汝所司。”[53]
其次,明清两朝女性文化教育方式多样,内容丰富。
在教育方式上,明清两朝女性文化教育主要有“家传”与“师授”两种形式。“家传”主要指父母或家族其他长辈亲自传授文化知识给女儿或晚辈女性。“师授”,主要指一个家庭或家族请女性或男子塾师来教育女儿或同族女子,即人们熟悉的明清社会私塾教育。如明清之际女诗人毛媞,为著名文学家毛先舒女,她“幼承庭训,刻苦吟诗”[54]。而明代女诗人吴琪则通过“延师教读”的方式获得文化知识:“幼即颖悟,五岁时辄过目成诵。父母见其慧性过人,为延师教读,髫龄而工诗,及笄而能文章。”[55]明清女性还有通过自学方式获得文化知识的例子。如晚明著名的“午梦堂”中女作家沈宜修就是通过自学成才的。她“幼无师承,从女辈问字,得一知十,遍通书史,将笈,遂手不释卷”[56]。而清代著名女作家恽珠所受教育方式则是“家传”与“师授”兼而有之:“年在龆龀,先大人以为当读书明理,遂命与二兄同学家塾,受《四子》《孝经》《毛诗》《尔雅》诸书。少长,先大人亲授古今体诗,谆谆以正始为教,余始稍学吟咏。”[57]
在教育内容方面,明清女性教育始终将政治、伦理教化摆在首位。她们首先要学习的是《内则》《列女传》《女诫》等讲说女性道德伦理的书。其次为中国古代男女童通用的蒙学教材,如《孝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诗词诵读、诗文创作与历史知识传授也受到重视,如《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而书法、绘画、音乐、棋术、佛老等诸多学问闺秀们也可兼及。明代女子夏云英“五岁能诵《孝经》,七岁学佛,背诵法华、楞严等经。琴棋音律,剪制结簇,一经耳目,便皆造妙”[58]。明代另一女性叶小鸾三四岁时,就由舅父沈自征口授唐诗与《花间》《草堂》诸词。“十四岁能弈,十六岁善琴,能模山水,写落花飞蝶,皆有韵致。”[59]清代著名女诗人钱孟钿,“幼读书,涉览不忘。尚书(其父钱维城官至刑部侍郎)为授《史记》、《通鉴纪事本末》,遂能淹贯故事。又授以《香山诗》一编,曰:‘此殊不难,试为之。'”[60]
明清两朝,在日渐多元的女性文化的互动与相生中,女子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和提高程度均远远超过此前的任何一个时期。传统文化与时代风尚相濡相生,共同培植出多元的女性文化生态;这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人生“新概念”与“新名词”或显性或隐性地影响着全社会的女性观念,为明清社会构建出女性培养的“理想范型”。这些“理想范型”既有传统的贤妻良母、烈女节妇,又有时代新特色的才女类群,此类才女类群为明清女性文化教育实践提供了清晰的规范和明确的导向,从而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不限于此,这些女性“理想范型”又有着巨大的社会效应,从而蔚成一种时代风气,砥砺出明清社会新的女性文化风尚。
时代语境之三:中晚明结社活动风行社会各界,文人诗文结社成为时代主潮之一。而清代文人诗歌结社仍不绝如缕,成为其时诗歌创作的一种常态。
我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诗歌结社起始于唐代。延至宋元,诗社、词社开始大量涌现,形成我国古代文人诗词结社的第一波高潮。明清文人承继前代诗词结社的文化传统,在文人诗词结社数量、规模、类型、文化品位、社群成熟指数等诸多文化质素上较之前代均有拓展与深化,从而蔚成我国古代文人诗词结社最为灿烂辉煌的“巅峰”时期。谢国桢在论明代文人结社风气之盛时说:“结社这一件事,在明末已成风气,文有文社,诗有诗社,普遍了江浙、福建、广东、江西、山东、河北各省,风行了百数十年,大江南北,结社的风气,犹如春潮怒上,应运勃兴。那时候不但读书人要立社,就是士女们也要结起诗酒文社,而那些考六等的秀才,也要夤缘加入社盟了。”[61]何宗美也说:“文人结社至明代而极盛。郭绍虞先生《明代的文人集团》所列达一百七十余家,其实,真正的情况尚不止于此。”[62]
就清代女子诗歌结社而言,明清文人诗词结社的大繁荣,既是一种历史构成与历史存在,又是一种时代语境,更是清代女子诗歌结社繁荣的直接推力与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