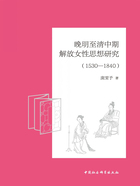
第一节 传统儒家女性观的源流与诠释
儒家,作为影响了中国士人几千年的一种文化传统,其内部是驳杂而多变的,“历史上并不存在统一的儒家,也不存在一脉相承的儒家传统”[2],由孔子奠基的儒家传统,其发展经过了“原生、衍生、变异、衰落”[3]几个阶段。作为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儒家女性观在历史发展中也表现为多元变化,为后人留下了广阔的诠释空间。
一 晚明以前儒家女性观的发展历程
儒家女性观的发展是一个较为宏大的课题,此处不对其进行详述[4],仅摘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献与对后世(尤其是明清时期)影响最为深远的观点加以论述,以粗略展现明清以前传统女性观发展的概况。
(一)先秦时期的女性观与性别角色定位
反映这一时期女性观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周易》《诗经》《礼记》及《仪礼》,这些经典奠定了后期儒家女性观发展的基础,也深深地影响了明清时期思想家女性观的形成。
在《周易》中,男女的地位以天/地、阳/阴的形式被明确固定下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周易·系辞上》),“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周易·谦卦》),其中男性处于天之位,天道表现为乾、阳、动、刚、贵、健等特征,而女性处于地之位,地道表现为坤、阴、静、柔、贱、顺等特征。这样一来,也就相应地形成了男/女、外/内的分工模式,即“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在此基础上,《易》进一步规定了女性的职责与本分,即“无攸遂,在中馈,贞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人嘻嘻,终吝”(《周易·家人》),若是逾越了这一界限,则是“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周易·坤卦》)。总之,《易》从哲学层面规定了坤之道,作为“阴”性的女性被赋予了一系列的特征与职责。
另一方面,《周易》哲学辩证的思维模式也使得其所描述的阴与阳、乾与坤之间有一种适度的张力,处于卑下地位的“阴”又是与“阳”共同构成“道”之不可或缺的因素,并且“阴”并不总是以一种固定化的模式处于下方,乾、坤二者都是有其内在活力的基本因素,所以阴阳之间有一种互补、互动的关系,并有着相互转换的潜在可能。这就使得《易》虽然规定了严格的性别角色分工,但却并没有把女性置于一个完全被动的状态,如“《咸》,感也。柔上而刚下,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周易·咸卦》),所指的是柔居上时,男女之间的一种交感,解经者常常以婚礼中的“亲迎”来作比。又如,“《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恒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周易·恒卦》),虽是刚居上的情况,但也强调刚柔皆应,才可恒久,而《序卦》对夫妇之道重要性的强调也由此而出。此外,《系辞下》云“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都显示出阴阳之间活泼泼的互动与转换关系。《易》哲学中阴阳之间的生动张力及其对夫妇一伦重要性的强调,也为明清思想家阐释解放女性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坚实的哲学基础。
在《礼记》及《仪礼》中,男女的社会性别角色以制度的形式进一步固定下来,《礼记·郊特牲》云“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奠定了“男女有别”在人伦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男女之别广泛地体现在成年礼、婚、丧、祭祀等各个方面。在成年礼上,男性行冠礼,女性行笄礼,“女子十五而笄”(《礼记·内则》),又“女虽未许嫁,年二十而笄,礼之,妇人执其礼。燕则鬈首”(《礼记·杂记》),笄正是女性许嫁从人所迈出的第一步。[5]在婚嫁上,婚姻六礼的礼辞中充分体现了男主女从的特色,《礼记·郊特牲》云“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强调了男女主从关系对夫妇之伦的重要性。[6]在婚姻制度上,还有需要特别注意的“三月成妇”一说,新妇要三月庙见之后才称“来妇”,才可以有祭行,这三个月也就是新妇的考察期,其间如果女性亡故,仍归葬于其父家。《礼记·曾子问》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记载,这也成为明清时期学者讨论贞女问题时重要的古礼依据。在丧服制度上,为父服重,为母服轻[7];妻为夫服重,夫为妻服轻[8];父系服重,母系服轻。在祭祀方面,丈夫主祭,妻子助祭,整个祭祀程序都体现出男性行礼开其端,女性继而从之的特色[9]。此外,在讨论“妇人不二斩”的问题时,《仪礼·丧服》云“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明确了女性的“三从”地位。总之,礼的规定进一步细化与强化了男女的社会性别角色,男主女从与男女有别的观念在各种礼仪细节上得到了详尽的发挥。
“思无邪”的《诗经》中则保留了大量反映男女情爱的诗篇[10],如朱熹所言:“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11]这些有关女性的诗歌,一方面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婚恋中女性的情感、心理及其地位,从男恋女的《关雎》到妇思夫的《卷耳》,从女子渴望爱情的《摽有梅》到反映婚姻不幸的《氓》,从描写女性美的《芣苢》到刻画女性具体生活的《葛覃》《采 》,等等,这些诗歌为我们今天了解古代女性的生活提供了非常生动的素材,展现出了当时朴素的婚姻爱情观念,也为明清进步思想家阐释其解放女性思想提供了经典依据,如唐甄以《白华》中“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一句来阐发“夫妇相下”之道,袁枚以“《诗经》好序妇人”来证明男女情爱之正当性;另一方面,这些诗歌也成了女性文学的源头与经典依据,如邹漪在《红蕉集》中指出“《三百》删自圣手,《二南》诸篇,什七出自后妃嫔御、思妇游女”[12],袁枚也强调“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13],尽管这种说法并不一定符合史实,但却的确是明清文人为女性作诗正名的一个有效策略。[14]
》,等等,这些诗歌为我们今天了解古代女性的生活提供了非常生动的素材,展现出了当时朴素的婚姻爱情观念,也为明清进步思想家阐释其解放女性思想提供了经典依据,如唐甄以《白华》中“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一句来阐发“夫妇相下”之道,袁枚以“《诗经》好序妇人”来证明男女情爱之正当性;另一方面,这些诗歌也成了女性文学的源头与经典依据,如邹漪在《红蕉集》中指出“《三百》删自圣手,《二南》诸篇,什七出自后妃嫔御、思妇游女”[12],袁枚也强调“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13],尽管这种说法并不一定符合史实,但却的确是明清文人为女性作诗正名的一个有效策略。[14]
(二)两汉时期对女性从属地位的强化
在宇宙论盛行的汉代,哲学上出现了“儒法合流”的走向,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与“人副天数”将“三纲”思想合法化,阳尊阴卑的思想被进一步固定下来。在《春秋繁露》中,董氏明确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天的权威性将君臣、父子和夫妇关系一并纳入一种模式化的固定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春秋繁露·基义》)。阴、阳在《易》哲学中的生动张力被取消,高下、尊卑的等级秩序成了一种人伦世界的“永恒法则”,作为“阴”类的女性被明确赋予了卑贱的类特征。[15]
东汉时期的《白虎通义》则将“三纲”思想进行了详细诠释,从理论上强化了女性的受压迫地位。《白虎通义》将女性之“三从”地位与其社会角色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男女谓男者任也,任功业也。女者如也,从如人也。在家从父母,既嫁从夫,夫没从子也”(《嫁娶》),“妇人无爵何?阴卑无外事。是以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人无爵》),夫妇二者的职责与地位则相应地表现为,“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也。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嫁娶》)。《白虎通义》也开启了夫妇在婚姻贞节上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妇人无外事,防淫佚也”(《丧服》),另一方面,“夫有恶行,妻不得去也,地无去天之义也”(《嫁娶》),表明妻没有去夫的权利。金春峰指出,“《白虎通》对夫权,作了更加绝对的肯定,对妇女的地位作了更加残酷的贬抑”,当然,《白虎通义》也讲到夫妻宗法情谊的一面,如“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下至庶人,其义一也”(《嫁娶》),“妻得谏夫者,女妇荣耻共之”(《诤谏》),但它不占主流,也不体现整个女性观的发展趋向。[16]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最早的女性史著作,即刘向的《列女传》。全书记载了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七种类型的女性形象,刘向有感于当朝“赵氏乱内,外戚擅朝”的危机而作此书,以正反两面的女性形象来劝诫与警示汉成帝,而这些人物的塑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的女性观。相比先秦儒家,刘向除了继承传统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定位外,其女性观还有一些突出的特点,如肯定女性才智与价值,强调母教的重要性,重德轻色,重义轻利,等等。一方面,其所刻画的女性形象总体上是多元的,相比后世仅仅强调节烈的《烈女传》,它充分展现了女性价值的多样性,如女性的才智、胆识、节义,等等,这也为明清时期思想家发掘女性价值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另一方面,其所刻画的单个女性形象又是缺乏张力的,由于刘向旨在树立正面榜样和反面典型,《列女传》所颂扬的女性往往具有让人望尘莫及的品德与智慧,而反面女性则成了“红颜祸水”的化身。这种简单的“二分法”,使得前者的高义品行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凝固化,产生一系列违逆人情的伦理异化现象,也使得后者成了“女祸论”观念的有力根据。而这些流弊,都成了明清进步思想家批判的基本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时期也出现了“女性的声音”,即班昭的《女诫》。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女教作品,对后世的女性教育有着极大的影响。《女诫》包括了以下七个部分:卑弱第一、夫妇第二、敬慎第三、妇行第四、专心四五、屈从第六、和叔妹第七,意在教导女性如何为人子妇、为人妻。班昭认为,出嫁的女性应该卑弱以事人,敬顺丈夫,曲从舅姑,谨修妇行,并肯定了“《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17]。女性对自身卑下地位的认同,其历史影响实则较之男性的声音要更为深远,因为班昭在当时以一名“成功女性”的身份对女性的类特征进行了强化,其代表性、权威性与女性情谊所伴随的认同感都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五四以来,以《女诫》为首的女教著作遭到了猛烈的批评。[18]恩格斯指出,“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19],我们进而可以说,女性对父权制的强化与认同,乃是女性的彻底妥协,正是这种妥协,让女性在更长的历史过程中甘于甚至乐于处于较低的地位。
班昭在序中说明了她晚年作此书的目的:
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沈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间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勖勉之![20]
不难看出,班昭所书写的正是她四十多年来为妇的心得,也是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基本生存指南,其目的正在于让家族的女性吸取前人经验,少走弯路。对于处于弱势的女性而言,寻求已有空间中的生存法则显然比争取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要来得容易,在这个意义上讲,班昭的《女诫》不过是女性对历史的一种顺应,或者说是各种合力作用下形成的自然走向与自觉选择。她也许不曾料到,这篇两千余字的劝诫对后世影响之大、之广、之深,以至于具有深刻解放女性思想的李汝珍在《镜花缘》开篇即引此为典训,以表明自己的“正统”立场。
(三)宋代对贞节观念的强化与性别特征的固化
宋代的女性观当然并不仅仅包含贞节观念,从周敦颐、二程到朱熹,众多哲学家都对阴阳乾坤之道进行了演绎和发挥,对两性关系的论述普遍地继承了《易》以来的“乾坤并建”与“阳尊阴卑”两种传统。在男女角色定位上,强化了先秦以来的“男女有别”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强调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与重要性。而这一时期理学的发展,则使得理欲关系愈加紧张,“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四书集注·孟子滕王公上注》),“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子语类》卷十三),天理与人欲处于二分的对立状态。对天理的过分推崇、对人欲的压抑,成了宋代女性观所根植的伦理土壤。
相比之前的女性观,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就是贞节观念的强化,最为著名的论述莫过于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21]一语:
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者,是己失节也。”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22]
我们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程颐事实上是意识到了男性的贞节问题的。此处已有男性贞节的考量,既然女性再嫁失节,那么男性娶再嫁者为妻也为失节。在后文中,程颐对男性再娶作了更为详细的阐释:
又问:“再娶皆不合理否?”曰:“大夫以上无再娶礼。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盖缘奉公姑,或主内事尔。如大夫以上,至诸侯天子,自有嫔妃可以供祀礼,所以不许再嫁也。”[23]
也就是说,程颐已经意识到,从理论上讲,再嫁与再娶同样都是对“从一而终”的违背。但他却赋予了男性再娶在现实中的可能性,对于大夫以下的男子,需要有人侍奉公婆、主内事,所以不得不再娶,而大夫以上有嫔妃可以来承担这些任务,所以没有理由再娶。
我们当然相信程颐是真诚地认为男女都应该守节,并且这相比于“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公然宣称男女的双重道德标准的确要更具说服力。[24]但事实上,这段解释不仅不能显示出程颐对男女两性在贞节问题上一以贯之的态度,反而更加清楚地反映出其在贞节问题上的双重道德标准:其一,不可再娶者有嫔妃可以替亡妻主内事,所谓终身夫妇,不过是纳妾制度保证之下的终身夫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男女一也”;其二,可再娶者是为着侍奉公婆、主内事等“不得已”的原因而再娶,反过来,女性因“孤孀贫穷”而无托,却要以“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来作极为严格要求,这实际上把男性家族之利益凌驾于女性的个体生命之上。[25]
此外,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中,男性不再娶并不会真正威胁其生存,而对于众多没有生活来源的女性而言,丧失了家庭的经济支柱,她们的生存可能受到威胁,因此,女性守节的阻力要更大。也就是说,对程颐而言,“终身夫妇”之约在理论上的确是针对男女双方,但“贞节高于生命”这样的要求则是仅仅针对女性的。而这两种要求,在程度上是有很大差别的。
在朱熹那里,对女性的贞节要求进一步强化,在其与吕祖谦所合辑的《近思录》卷六之《家道》中收入了程颐关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对话。在写给门人陈师中的信中,朱熹亦劝其不要让寡居的妹妹改嫁,“朋友传说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26]。可见,朱熹已经将程颐的观点在实践中推进,在家族以外的领域劝诫寡妇守节。
不过,在宋代社会中,理学家的贞节观的实际影响仍是比较微弱的[27],即使是倡导“贞节高于生命”的程颐亦对其甥女的改嫁表示赞同,“与前朝和后世相比,宋代妇女因丧夫或离婚而再婚都并非更不合法。强烈反对寡妇再婚的法官也不得不维护再婚的合法性”[28],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语的更大影响实际上是在之后的明清时期才得以呈现[29]。当然,这种影响的非直接性也并不足以为宋儒的贞节观进行有力的辩护,因为明清严苛贞节观念形成的理论源头终归要追溯到宋代理学家这里[30],所以清代学者钱大昕、钱泳等人为女性改嫁辩护时,也都不约而同地批评了宋儒的贞节观。
宋代的女性观除了在贞节观念上更加强化,女性的性别特征也趋于固化,我们可以从朱熹的女性观中略窥一二。朱熹的女性观既体现在其与学生刘清之共同编撰的《小学》一书中,也体现在其为女性所作的墓志铭中。此外,在其《朱子语类》《诗集传》中也有所体现。
虽然自先秦以来,在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建构中一直强化着男女之别,但到朱熹这里,可以说进一步固化了女性的性别特征,女性无论是在思想上、才学上以及能力上,都被看作与男性不一样的“阴类”,而对女性家庭作用的单方面强调,则进一步固化了女性的类特征,与男女平等有了更远的距离。
在哲学思想层面,朱熹认为女性与男性在气禀上有着根本的区别,如其与门人的一段关于气禀的对话,“问:所以妇人临事多怕,亦是气偏了?曰:妇人之仁,只是流从爱上去”[31]。又如程颐曾谓范淳夫之女“此女虽不识孟子,却能识心”,但朱熹则对此评价为:
人心自是有出入,然亦有资禀好底,自然纯粹。想此女子自觉得他个心常湛然无出入,故如此说,只是他一个如此。然孟子之说却大,乃是为天下人说。盖心是个走作底物。伊川之意,只谓女子识心,却不是孟子所引夫子之言耳。[32]
朱熹认为女性与男性在认知能力上有着根本的区别,所以他强调“心却易识,只是不识孟子之意”。在朱熹这里,女性虽然在情感、心性上有值得肯定之处,但并不具有形而上学的思辨能力,更不能真正地把握最高的“道”。
这种差别在其为女性所作墓志铭中也有所体现,众所周知,朱熹对佛教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也反对男子礼佛的行为,但在女性身上,他不仅容忍女性礼佛,还对她们的佛教信仰常常持赞赏的态度,如其在《太孺人陈氏墓志铭》中写到,“晚年好浮屠法,得其大指,遂不复问家事。恶衣菲食,逾二十年。而忧人之忧,赈其恶穷病苦,虽极力不倦”[33],在《宜人黄氏墓志铭》中写到,“初好佛书,读诵拜跪,终日忘倦”[34],在《建安郡夫人游氏墓志铭》中写到,“亦颇信尚浮屠法,娠子则必端居静室,焚香读儒佛书,不疾呼,不怒视”[35]。朱熹对女性佛教信仰的宽容态度,有学者认为这与朱熹以坤道的诚敬养成女性道德人格的工夫路径相一致[36],信佛作为女性私领域的行为,与男性在公共领域的纲纪规范是相分离的。
在具体的女才层面,朱熹对女性教育的肯定也是有条件的。当其与人论及女子教育时,有这样一段记载:
问:“女子亦当有教。自《孝经》之外,如《论语》,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何如?”曰:“亦可。如曹大家《女诫》,温公《家范》,亦好。”[37]
显然,朱熹并不反对女性接受教育,在其所作的女性墓志铭中,所书写的对象也大都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与较强的阅读能力。但朱熹更为看重的不是女性才学本身,而是其为家庭及教育子女服务的功用。所以他所认可的女性教育范围是比较狭隘的,主要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教女性如何更好地为父系家庭服务的经典女教。
在夫妇伦理上,朱熹继承了传统儒家女性观对夫妇之别的强调,警惕夫妇之间的亲密无间的情感。在《答口易简》中,其言“《小学》之后,自明伦五段……明夫妇章全在一个‘别’字。……始读婚礼,万世之始,至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汉武帝溺于声色,游燕后宫,父子不亲,遂致戾太子之变。此亦夫妇无别而父子不亲之证”(《朱子文集》卷六十四),可知朱熹把“男女有别”放在了家庭伦理中的重要位置。在朱熹《诗集传》所注解的《诗经》中,对男女之情多有戒备,即使是家庭之内的夫妇关系,朱熹也强调距离的保持。比如《郑风·女曰鸡鸣》曰:“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朱熹对此注解道:“此诗人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词。言女曰鸡鸣,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则不止于鸡鸣矣。妇人又语其夫曰:若是,则子可以起而视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烂然,则当翱翔而往,弋取凫雁而归矣。其相与警戒之言如此,则不留于宴昵之私,可知矣。”[38]实际上,朱熹在其婚姻生活中也践行着这样一种“夫妇有别”的伦理关系,其文集中绝少见到对妻子刘清四情感的提及,朱熹的妻子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一生共生养了三男五女,于四十四岁时在劳累与贫困中去世,在刘氏病重的一年多时间里,朱熹也基本不在身边。妻子去世后,朱熹除了伤感悲痛外,对家庭琐事、养育子女等更是感到手足无措,虽然二人夫妻感情平淡,但在刘氏去世的二十五年间,朱熹也并没有续弦。[39]
朱熹的女性观代表了儒家女性观的正统典范,无论是其对“阳尊阴卑”的强调,对女性才学的定位,还是对“夫妇有别”的书写与践行,都让女性的性别气质更加固化,让女性成了与男性差异更明显的“人”。
总之,先秦至宋代的儒家女性观逐渐趋于稳定,也逐渐趋于单一。牢固的性别分工、严苛的贞节观念,都使得女性处于较低的位置,尽管其中有对抗夫权、父权的种种张力存在,尽管作为理论而存在的女性观并没有完全下放为实际生活中对女性的要求,但其仍然引导了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女性地位的基本走向,也对晚明至清中期解放女性思想的出现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明清进步思想家对汉儒、宋儒所强化的纲纪与天理颇有微词;另一方面,他们又从原始儒家那里找到了诸多思想资源,作为其阐释解放女性思想的理论基础。
二 儒家女性观的诠释与评价
尽管历史的发展中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统一的儒家女性观,但我们仍可以尝试概括出儒家女性观内部相对稳定的因素与两种不同的诠释路径,这些基本因素也派生出了后世对于儒家女性观的不同理解及评价。
(一)两种诠释路径
《说文》中对妻、妇二字的解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诠释儒家传统中女性处境的两个维度。一方面,《说文》曰“妻者,妇与己齐者也。从女,从屮,从又。又,持事,妻职也”,一般来讲,“妻”反映的是女性与男性平等的一面。[40]从哲学上讲,也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合德”,“刚柔相易”。在这个意义上,夫妇二者的关系是平等的,尽管内外分工不同,气质、性格各异,但二者相互需要、互为一体,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相互转换。妇对夫之“从”,更多是先后顺序上的跟从,而非绝对地服从。这种诠释强调阴阳之间的张力、变化与互动,阴阳的关系中渗透着一种生命力。
另一方面,《说文》曰“妇者,伏也。从女持帚,洒扫也”,段注云“妇主事人者也。《大戴礼·本命》曰‘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女性与阴、坤、地道、臣道、柔、弱等概念相联系,进而下滑为伏、从、低、贱等带有明显价值倾向的评价。而男性则与阳、乾、天道、君道、刚、强等概念相联系,进而上升为扶、主、高、贵等带有明显价值倾向的评价。从哲学上讲,也就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在这个意义上,夫的地位是完全高于妻的,男女的等次秩序是固定不变的,妇对夫之“从”强调的是从属与服从之义。
然而,这两种诠释路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可以明显区分的,其边界往往是模糊的,二者或隐或显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儒家女性观的基本内容,所以我们很难简单地将其中之一作为儒家女性观的诠释代表。此外,两种诠释路径也有基本一致的设定,其一,“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角色设定;其二,都强调“男女有别”,此处的“别”一则为别异,即男女之身、心等方面的差异,一则为分别,即男女之别嫌,大防。这都是自始至终贯穿于儒家女性观中的。
(二)评价与对话
在评价儒家女性观时,超越五四以来的压迫/反抗路线,对儒学持同情理解态度的学者一般认为,原始儒家对女性是较为温和的,而汉儒、宋儒所倡导的凝固化的礼教纲常才造成了女性受压迫、受束缚的状况。但对于原始儒家女性观中男女地位是否平等,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儒家女性观等问题,学界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儒家传统中(主要是原始儒家)的男女虽然分工不同,但在地位上是比较平等的,并常常将其作为理想两性关系的模型来看待,以林语堂、杜维明为代表。林语堂指出,“儒教意识到这种男女的不同有益于社会的和谐,或许在此儒教已经非常接近真理。然后,儒教也给予妻子与丈夫差不多‘平等’的地位,但妻子地位多少低于丈夫,不过仍是平等的配偶,正如道教中代表阴阳的两条鱼,相辅相成……男女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对妇女的束缚,而是意味着关系的和谐”[41],并且,“在实际生活中,妇女并没有被男人压制”[42]。杜维明则主张将“三纲”与“五常”区别对待,认为“三纲”的观念是对孟子“五常”观念的偏离,而孟子那里的“夫妇有别”是以相互性为基础的,因此“说儒家传统中的妻子像一种财产一样归丈夫‘所有’是错误的。妻子的地位不但由其丈夫的地位决定,而且也由她的家庭的社会地位决定。……在通常情况下,妻子往往掌握着日常生活的决定权。儒家的妻子具有顽强的忍耐力。……妻子并不受制于丈夫,她与他是平等的”[43]。
也有学者则倾向于认为,应该正视儒家历史上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比如李晨阳就坦白承认,“无论我们怎么看,在中国受儒家影响的很长时期里,妇女受压迫、受歧视的事实是不能否定的”[44],但是,他也强调这种压迫与歧视并不具普遍性和绝对性,儒家传统仍然“为妇女的道德发展和社会发展参与留出了一定的空间”,进而为“妇女未来的发展和实现男女平等提供了一个起步点”。[45]在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考察时,李晨阳还指出,孔孟原始儒家那里,虽然对女性有过一些引起争议的表达,但“我们至多可以说这些早期儒家经典作家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当时社会对妇女的歧视态度,而没有证据说它们制造了这种态度”,而汉代的董仲舒把阴阳哲学引入儒家,才导致男尊女卑被广泛地固定下来。所以,李晨阳认为应该抛弃后儒歧视女性的思想,回到原始儒家,从孔孟思想出发,把儒家伦理学改造成不歧视妇女甚至支持男女平等的伦理学。[46]基于这种基本认识,李晨阳试图对儒家在女性问题上的缺失作出回应,他将儒家与女性主义关爱伦理学进行比较,指出了二者的相似之处。[47]郑宗义则不同意这种对孔孟儒学与后儒区分开来的对话策略,而是主张将不同的诠释传统都视作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并解构其中的封闭成分,重释其普遍的开放成分,认为这是儒学得以与女性主义对话的有效策略。[48]郑宗义也将儒学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进行了对话[49],并指出二者可以进一步攻错之处,其对话的目的在于“借着女性主义的某些睿识来善化自身,使儒学成为一套能够包容女性声音、体现两性平等及促进两性相互协调的思想”[50]。
笔者认为,这种诠释与对话,对于儒学的丰富和发展而言,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样的对话也可能导致一种危险,这要从女性主义关怀(关爱)伦理学内部的分歧及其招致的批评说起。关怀伦理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由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最早提出,《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和妇女发展》是其代表作。吉利根通过对“不同的声音”的描述,对道德发生论上的“男性”模式提出了挑战,并在研究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道德视角,即公正视角与关怀视角,虽然她的研究证明男女都可能有这两种视角,但“她的确是从对女性的经验研究中发现关怀视角的”,而后来的很多研究者则直接将关怀视角与女性相联系。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则是关怀伦理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她从伦理学层面将关怀伦理学进行了理论化和系统化,并明确将女性与关怀联系起来,认为大多数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联系情境、基于关怀、注重情感与感觉。[51]
将女性的视角进行凸显,其本意当然是要让学者在研究中注意到“女性的声音”,并以“关怀”来批评仅仅强调“公正”的缺失,但将女性与关怀视角相联系,将导致女性/男性、关怀/公正的二分,可能陷入一种本质主义的话语中,对女性的发展与两性的沟通都造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不同的声音”也招致了很多的批评[52],而关怀伦理学的内部也发展出了不同的理论走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琼·C.特朗托,她认为将女性与关怀联系在一起是错误的,进而试图建立一种超越性别的关怀伦理学。特朗托认为吉利根的关怀伦理学是典型的“妇女道德”理论,这种道德性别化的策略可能导致很多危险,因此,为了找到“关怀”的定位,她重新区分了一种二元伦理学理论,即康德式的“道德观”理论和“情境道德”理论,关怀伦理学显然属于后者,而这一区分,与性别没有关系。[53]
学者将儒学与女性主义伦理学进行对话时,往往是与吉利根、诺丁斯的理论进行比较与对话,而非超越性别界限的关爱伦理学。与女性主义伦理学进行对话,对于拓展整个儒学的包容性而言,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从解放女性的角度来反思,将儒学与强调道德性别化的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进行对话,并不能真正地拓展儒家女性观的内涵,或者说,这种对话从根本上仍是在用一种相近的现代理论来诠释传统的儒家女性观,而并不能生长出儒家女性观的转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在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内部已招致深刻批评的“妇女道德”与儒家传统所刻画的“理想女性”的品质具有极大的相容性,男/女、公正/关怀、自主/关系、独立/依赖的二分法正是传统儒家女性观男/女、外/内的性别角色分工中可以自然生长出来的二分状态,正如“妇女道德”可能导致女性重新陷入被压迫地位,或者导致男女道德的一种二分对立,传统的儒家女性观也面临同样的危险。因此,道德性别化的“关怀”视角并不能促使儒家女性观取得实质性的发展。[54]
回过头来,我们再反观晚明至清中期思想家对女性问题的讨论,通过对本土解放女性思想资源的开掘,也许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儒家女性观自身的张力、内部发展及其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