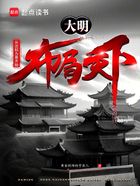
第22章 沈一石的命门
听沈一石准确叫出自己的字,郑榕的眼神多了些玩味。
沈一石何等人精,自然也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却对琴谱动心不已,并未回避目光。
两人对视一眼,郑榕笑道:“此物是南京好友所赠,宝剑配英雄,姜白石处江湖不忘君国,是难得的高洁之士,词曲双绝,正与沈兄相称,还望笑纳。”
明知是奉承,沈一石却难有恶感,反而心生知己难求之感。
他精通音律,尤爱嵇康的事在浙江不是秘密,但世人不知,屡试不第、终身未仕的姜夔才最让他深感同病相怜。
这句“处江湖不忘君国”几乎是直直戳中心坎,让他喜不自胜。
他郑重地接过琴谱,神色微动:“俗语讲无功不受禄,贤弟如此厚礼谬赞,愚兄实在愧不敢当。”
说着,他对身旁管事叮嘱几句,不一会儿就见对方捧着个绸布包快步赶回。
沈一石从中取出一长条木盒,轻轻拈出里面的毛笔。
笔杆是多年的紫檀,较寻常毛笔略略粗上少许,精雕着仙鹤。
沿笔杆往下看,两头是象牙,笔套则用和田玉雕琢而成,晶莹剔透。
沈一石双手奉上,说道:“不知贤弟所爱何物,只得以此相赠,盼贤弟诗书传家,早日及第登科!”
仙鹤乃一品文官补,这是名贵之物,也是标准回礼,读书人都不会抵触。
但正如他自己所说,还是落了下乘。
在商场上便是失了先机。
洒脱的他坦然应下,郑榕也不拘礼,欣然接受,于是宾主落座。
一来一回,双方亲近了几分,主动权也自然落到郑榕手中。
沈一石抿上一口白水,问道:“贤弟一定不只是为了结识一番,不知可否明示?”
“沈兄慧眼,弟今日冒昧前来,确有件要紧事。”郑榕说,“沈兄想必已经知道改稻为桑的事了,不知有何打算?”
“改稻为桑是国策,沈某依令行事,定当竭力增产丝绸。”沈一石不动声色道。
说起正事的他换了自称。
郑榕早知会有如此答复,轻声说:“沈兄的丝织作坊名满天下,又是增产主力,不知可否带我长长见识?”
“这有何不可?”沈一石从容起身,“贤弟请随我来,我这宅院的前院便是二十年前的第一家作坊。”
-----------------
作坊里,声响此起彼伏,汇作浪潮。
一丈宽的织机横着排了六架,中间是一条能容纳两人并行的通路,顺着走下去,足有三十排,织着不同颜色的丝帛。
“这样的织机搭配江南最好的织工,每天两班轮着织,一天可织六尺。沈某有三千多架织机,每年可产丝绸二十万匹。”
虽是背靠江南织造局,却这家业也绝非常人所能创下,沈一石隐隐有些自得。
郑榕对此早有预料。
虽然足智多谋,但自命清高又抛不掉商人本色的沈老板比官员更好对付。
“沈兄气魄超群,还能不忘初心,守着发家之地,当真是名士本色。”
“哪里,物尽其用而已。”沈一石摆手谦虚道,眉眼舒展,显然很受用,“这里不是议事的地方,我们换个去处。”
投桃报李的他没再去客厅,而是将郑榕带到了琴房。
坐在那张名贵古琴之后,他的心绪也平静下来,直率道:“作坊随时可以再建,要增产丝绸,桑田和生丝才是关口。”
“这正是家父所想。”郑榕说,“既要购置桑田,又要增设作坊,沈兄负担不轻。”
“愚兄为织造局经商,难处再多也得想办法克服,就像我这些织机绸行,再多也都是为宫里和各位大人开的。”
“这话是关键。”郑榕点头道,“沈兄兢兢业业多年,布衣素食,如今又要为国策殚精竭虑,着实令人敬服。”
沈一石矜持地一拱手,没说话。
郑榕话锋一转道:“可惜沈兄之才,尚且不能为己谋身。家父时常叹惋,今日听沈兄此言,弟也深有同感。”
这话说得沈一石糊涂了。
浙江上下拿钱从不手软,郑泌昌这个布政使每年就八万两,何出此言?
看郑榕的表情,他有了猜测,正色道:“沈某乃官商,尽心做事是本分。”
“既是本分,也是功劳和苦劳。”郑榕朗声说,“改稻为桑国策推行在即,沈兄就不想为自己谋划吗?谋国先谋身,姜白石固然可敬,却也是前车之鉴。”
“……!”
这话说的直白,打乱了沈一石的判断。
他缓缓睁大眼睛,甚至忘了该坐下,心里回荡着刚刚的话。
若姜夔那份棋谱是送到心坎,这前车之鉴的表述就是说清了他的心声。
他做不到嵇康那般洒脱出世,又深感如姜夔般求入世而不能,两番知音之语,让他心头激荡,以至于又一次略微失态。
沉默许久,他缓缓问道:“贤弟以为怎样才能谋身?”
这别扭的做派让郑榕心底一哂。
不论前世印象,还是现场过招,沈一石的弱点都正如自己所料。
确定把准了脉的他循循善诱道:“生意之道重在账目,沈兄的作坊都在钱塘,若能将作坊开到各县……”
沈一石外号铁算盘,论起生意是天下头等的精明人,转眼就猜到了后半句。
“分散布局,账目灵活,里外不过多些损耗,于我百利无一害。”他沉声说,“可这于改稻为桑何益?贤弟为何如此谋划?”
郑榕笑着竖起两根手指:“沈兄此言恕我不能苟同。依我看至少还有两个益处。”
“哪两个?”
“一是稳定市场。沈兄开设作坊,便可避免胥吏豪族产业一家独大,既能近水楼台收购生丝,又能解百姓之忧,助力国策。”
“另一个呢?”
“另一个自然是在商言商。改稻为桑多产的生丝,浙江吃不下就要外流,若能确保丝价平稳,在湖广也可以发展丝织。”
郑榕成竹在胸地说,接着不急不躁地望向沈一石,并不急着等待答复。
因为他很清楚,沈一石有着游移在文人和商人之间的“文青病”这个命门。
握住这个命门,这位眼光长远毫不逊色郑泌昌、杨金水的豪商就逃不出掌心。
事态发展也正如他预计那般,得了“公私兼顾还能为朋友行方便”这个台阶的沈一石几乎没怎么犹豫,点头道:
“贤弟所言,着实令愚兄豁然开朗。但要真想施行,还不免要实地考察一番。”
心中暗道一声果然,郑榕爽朗道:“沈兄若有此意,淳安是个好去处,改稻为桑首站就在那里。”
“承蒙美意,愚兄一定仔细斟酌。”沈一石拱手谢道,心中已然盘算起来,表面上却还维持着文人雅士的矜持与从容。
郑榕对这心思了如指掌,客气道:“实不相瞒,愚弟还有个不情之请。姜白石的词曲虽好,奈何弟与友人皆不通音律,至今未能听到大家演奏,不知沈兄可否……”
这番话给足了面子,更让自认为是清流雅士的沈一石心花怒放。
不多时,悠扬的旋律就在琴房回荡。
起初有些生疏,很快便纯熟起来,伴着婉转的越调南音,唱出词人的心绪。
郑榕神情专注地欣赏着,时而露出惊喜之色,心里想的却是另一回事。
他的目光落在了墙角。
那里码着一排不起眼的木箱。
他至少有七成把握,那里面装的就是足以震动朝局的罪证。
哪怕是为了老爹和全家的性命,也不能把他逼到玉石俱焚……
暗暗感慨一声,他站起身来,赶在一曲奏罢的间隙击节叫好。
沈一石的脸上也露出自矜之色。
他这辈子缺两样东西。
一样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另一样则是来自士大夫的尊重。
今天,在郑榕身上,他同时得到了这两样求而不得的“珍宝”,恍然有天人之感。
“知己难遇,怎能不喝酒?拿酒来!”
激昂的喊声透着魏晋狂士的洒脱。
郑榕附和着走上前,心中暗暗腹诽:
老文青确实比那些老狐狸好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