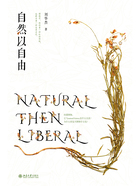
走近分类学,习惯规范性描述
《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植物分类指南》是英国皇家园艺学会(Royal Horticulture Society,简称RHS)为园丁、园艺师、植物爱好者准备的一部入门性同时兼具系统升级功能的手册,非常实用,在行业内一定程度上起规范作用。
入门,是指内容并不高深,书中主要讲述75个常见“科”的形态和分类基础知识,它是入门者的好教材;升级,是相对于老读者而言的,他们已经熟悉书中的基础知识,但是对于原来使用惯了的分类系统可能要更新(update)一下。系统升级比较有讲究,不能太迟亦不能太频。太迟则落后于时代,显得不自然;太频则会不稳定,造成混乱。从头学习新系统,白板一块,反而好办。但是对于大批业内人士,升级有时是折磨人的过程。克服惯性或惰性,需要做功,频繁升级会浪费精力。
那么,能不能把分子生物学的新成果彻底应用于园艺学,立即淘汰所有不那么准确、不那么科学的术语和理论呢?不能。一是做不到,二是那样做还有相当的危害,比如可能割裂了文化传统,让后来者看不懂历史文献,也让这门学问远离直观和“生活世界”。分类学是非常讲究历史和文献引证的学问,在这一点上它有点像文科。举个例子,如果新来者只记住了马先蒿属植物分在了列当科,虽然时尚、合理、科学,却是不够的,还要知道它原来分在玄参科,这样才能很好地利用人类辛苦积累起来的知识。对于柚木属、紫珠属、大青属也一样,既要知道它们现在分在唇形科,还要知道它们原来分在马鞕草科。人类对自然物的描述和分类,是不断演化的。对待分类系统,可以多一些人类学视角的宽容,不宜“五十步笑百步”。植物分类学是不断“自然化”的过程,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分类系统都是自然与人为两种因素组合的结果,即使那些打着“自然分类系统”旗号者也不例外。整体上看,APG系统相对于恩格勒系统和哈钦松系统要更自然,恩格勒系统和哈钦松系统相对于德勘多系统和林奈系统更自然。林奈系统公认是“人为系统”(其实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判断),但不等于其中不包含自然的因素,其实它不是纯粹的人为系统,即使中世纪的、古代的及日常的分类方案也包含自然的因素。
园艺学(horticulture)属于古老的应用植物学,与同样古老的药用植物学、食用植物学等类似(但与20世纪以后发展起来的一批新的应用植物学不同),这样的学科非常讲究可操作性,对学理、还原论方法并不是特别讲究。通俗点说,辨识清楚、种好花、置好景最为重要,搞清楚背后的机理不是第一位的。道理讲出一大堆,认不出物种、花园很难看、植物半死不活,那肯定不成。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从业者不需要学习很多科学,只要掌握足够的技术、技巧(不限于植物方面,还涉及土壤、气候等),辅之以一定的艺术,就可以做好园艺。但是,事情也在变化之中。在现代社会中,技术与科学分形地(fractally)交织在一起,技术进步直接与科学进展联系在一起。基础科学落后,园艺也不可能做到先进。现代的园艺学高度综合,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全部包括,虽然以后者为主;在园艺实践中,科学、技术、艺术、宗教、美学、文化传统等,一个也少不了,基础扎实才有底气、后劲。
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是世界著名的学术组织,学会成立于1804年,相对于其他学术组织成立时间不算很早,但对于与生命相关的学科来说,已经算早的了。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网站列出此组织所从事工作的“四I指导原则”:Inspire, Involve, Inform, Improve。非常好记,翻译成汉语大致是:激励、参与、通报、改进。眼前的这部书主要涉及第二和第四两条原则,也可以说与第三条有关。
此书以“科”(family)为主要单位来叙述植物系统树或者谱系,讲述各种植物知识。不过,“科”的概念在植物学发展史中,很晚才出现。林奈时代非常重视“属”和“种”,但无“科”的概念。德勘多、林德利之后,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科”的分类层级,而且显得越来越重要。对于初学者而言,“科”比“属”和“种”更为重要,宜优先学习。对于栽培植物,初学者不宜一下子就“深入”到“种”或者“种”以下的分类层级,因为园艺植物杂交厉害、来源复杂,分类非常困难,勉强为之可能徒增烦恼。“属”的数量相对于“科”的数量,多出许多,不利于初学者宏观“建筐”(打造出抽屉或文件夹)把握所面对的新植物。因此,这本书也是以“科”为主要层级进行示范的。
这是一部比较特殊的图书,翻译水平相当程度上将决定这部书中文版的价值大小。水平不高的翻译或马马虎虎来翻译,对于这样的图书,还不如不翻译。这本小书,就内容本身而言,阅读并无难度,但是翻译成汉语也并非易事,想做到完美更是困难。一是专业术语和植物名字太多,名词翻译在科学上做到合规、精准比较难。合规就颇难把握,有许多不同的规则,究竟以哪个为准?翻译中要选择规则,尽可能符合规则,还要打破过时的陈规。二是中国自己的园艺文化非常丰富,加之中国的植物种类众多,这给外来植物图书的中译增加了文化衔接的困难。此困难甚至大于前者。假如中国园艺不发达,假如中国植物种类本身就很少,翻译外来植物图书反而相对容易,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由刘夙翻译此书真的极为合适,一是他有较好的植物学基础,二是他熟悉命名法规,对植物分类和植物中文名字有特别的钻研,三是他做事非常认真,四是他有较丰富的图书翻译经验。刘夙与刘冰等人长期致力于植物科属规范译名和APG、PPG的普及传播工作,维护着“多识植物百科”网站,做了许多基础性的“积德的”工作。
我相信,在中国此书会受到欢迎。如前所述,它非常适合两类读者使用,一类是背景并不深厚的植物学爱好者,一类是相对专业的植物学工作者或园艺工作者。如果吃透此书的内容,真的可以把植物学知识和对植物的精确描述升级到一个新的平台。由这个平台再出发,情况将会很不同。
最后说点并非完全无关的闲话。学习园艺,必然想着亲手尝试。但是,个体不宜亲自到山上采挖野生植物,一是法律、法规可能不允许,二是挖了也通常栽不活,白白糟蹋植物。中国与英国的气候非常不同,即使是中国原产的许多植物(特别是高山植物),在中国的平原地区、城市中也是非常难以成活的,却反而在遥远的英国等异域国家相对容易成活!比如杜鹃花科、报春花科、罂粟科、兰科的许多植物都如此。这没办法,很难改变。耗资建立特别的温室可以部分解决问题,但很难持久,通常得不偿失。栽了死,死了栽,进入恶性循环;人人都想试一试,对野生植物的破坏力度可想而知。“迁地保护”也不大靠谱,虽然这类课题在申请项目时比较容易立项。比较好的习惯是,喜欢某类植物,到野外在原地观赏。家庭要做园艺,宜多选用比较皮实的种类,尽可能使用本土种,不要过分迷恋外来种。对于自己不再需要的园艺植物,在抛弃前先要主动灭活,避免物种流入野外,造成可能的生态风险。
2019年9月8日于北京西三旗
(罗斯·贝顿,西蒙·莫恩.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植物分类指南:75科常见植物的鉴赏与栽培.刘夙,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