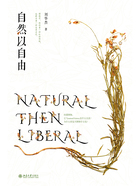
博物学家古尔德的坚持
1973年秋季的一天,古尔德(Stephen J.Gould,1941—2002)接到美国《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杂志主编特恩斯(Alan Ternes)的邀请,由此开启了长达近三十年的漫长写作计划。当时他就说,杂志上的专栏随笔从1974年1月启动,计划写到2001年。专栏名称“这种生命观”(The View of Life)看似平常,却是有典的,特指达尔文意义上的演化生命观,语出达尔文《物种起源》末尾“There is grandeur in this view of life”(这种生命观优美壮阔)的叙述。在纯学术上,古尔德的贡献主要是1972年与埃尔德里奇(Niles Eldredge,1943—)一同提出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演化理论,其核心论点当然不是彻底否定达尔文的理论,而是在细节上丰富、修正达尔文的思想。古尔德撰写此专栏也是在向前辈博物学家达尔文致敬。顺便一提,宾厄姆顿大学演化生物学与人类学教授威尔逊(David Sloan Wilson)有一部书《达尔文的生命观:有待完成的革命》(This View of Life:Completing the Darwinian Revolution),正标题也借用了达尔文的这一修辞。
在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古尔德的专栏文章每月一篇,从未耽搁。从1977年第一部结集《自达尔文以来》开始,以平均三年一部的节奏出版的“博物沉思录”(也可以称“自然启示录”,但不应是“自然史沉思录”)丛书一部接一部面世,好评不断。到2000年出到第九部《马拉喀什的谎石》,事后看它应当是倒数第二本,但是当时的副标题就是Penultimate 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倒数第二部博物沉思录),也就是说,古尔德心里有数,他很清楚自己持续甚久的写作计划还剩下一部就将彻底收工。“2001年1月庆祝千禧年的时候写完了不多不少300篇专栏文章”;古尔德编好I Have Landed这部文集(第十部也是最后一部,2002年出版),整个专栏写作计划全部完成,自己也撒手人寰。Landed,到岸、着陆、完事,意思相关。回想几十年前他的话,或许一语成谶。
是什么力量推动一个人把一个专栏写了近三十年,每月一篇,风雨无阻?别说那么久,坚持三年都比较困难。注意,这期间古尔德并非只做这一件事,他要教书、做研究还要写其他各种图书。真的很难回答。先不论内容和文笔,单凭时间和数量这一项,古尔德就名垂青史,恐后无来者。这十部文集,几乎本本畅销,屡屡获奖,它们分别是:
1.《自达尔文以来》(Ever since Darwin: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1977(首版时间,下同)。
2.《熊猫的拇指》(The Panda’s Thumb:More 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1980。
3.《鸡牙和马蹄》(Hen’s Teeth and Horse’s Toes:Futher 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1983。
4.《火烈鸟的微笑》(The Flamingo’s Smile: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1985。
5.《为雷龙喝彩》(Bully for Brontosaurus: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1991。
6.《八只小猪》(Eight Little Piggies: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1993。
7.《干草堆中的恐龙》(Dinosaur in a Haystack: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1996。
8.《莱昂纳多的蛤山与沃尔姆斯大会》(Leonardo’s Mountain of Clams and the Diet of Worms),1998。Diet指宗教大会,Worms是德国一地名。
9.《马拉喀什的谎石》(The Lying Stones of Marrakech:Penultimate 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2000。
10.《我到岸了》(I Have Landed:Splashed and 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外研社”本意译为《彼岸》),2002。
据我所知,三联书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几部。到目前为止,上述作品仍然有若干部没有中译本。中国科学界、科学文化界、科普界、科学传播界、出版界对古尔德的大名并不陌生,为何不把这十部出齐了?
古尔德的作品绝非只有这些,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专业论文和专著,如《演化论的结构》《人类的误测:智商歧视的科学史》《间断平衡》《奇妙的生命:布尔吉斯页岩中的生命故事》《刺猬、狐狸和法师痘:缝合科学与人文之裂隙》《时间之矢和时间循环》《追问千禧年:世纪末的理性探索》《生命的壮阔:从柏拉图到达尔文》等。
古尔德与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赫胥黎(Julian Huxley,1887—1975)、劳伦茨(Konrad Z.Lorenz,1903—1989)、迈尔(Ernst Mayr,1904—2005)、威尔逊(Edward O.Wilson,1929—2021)一样,都是最近一百年间最杰出的博物学家。不过,在现代社会中这些学者不会只有一个身份,他们还有古生物学家、林学家、遗传学家、动物行为学家、进化生物学家、昆虫学家等可以登上大雅之科学殿堂的专业名号,这些名号会大大掩盖博物学家的身份。好在至少上述诸位大师,他们敢于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就是博物学家,威尔逊甚至把自传的书名定为Naturalist。不过,上述一连串学科都属于自然科学之中并不光鲜的博物类学科,在热衷强力、速度与征服的大背景下,它们也只好处于科学圣殿中不太重要的位置,跟数理、控制实验及数值模拟传统相比,这类研究工作被认为相对肤浅。
博物学家写随笔,是早有传统的,但是到了现在,这个传统的延续遇到了困难。一是各类学术不断专门化,泛泛而论确实有点儿不痛不痒,深入一些又无法吸引普通读者。二是学者写多了这类东西会受到同行的排斥,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有时是出于嫉妒(“凭什么你那么风光,受大众欢迎?”),就像当年纳博科夫的画像上了《时代》周刊封面让许多昆虫学家不爽一般。古尔德也不例外,但他出于某种责任或使命坚持下来了,为人们留下一笔宝贵的散文遗产。如何给这种写作定位,是个难题。不仅仅在中国会遇到这个问题,在美国、在英国也一样。首先,这类随笔字里行间可能包含重要的原创学术思想,不仅仅是文学渲染和知识转述。历史上也的确有学者把一些重要思想不经意地写于通俗文本中,甚至写在脚注中。达尔文、古尔德、马古利斯、道金斯、威尔逊的散文中确实包含重要的学术思想,其重要性不亚于一本正经的期刊学术论文。其次,这些文字的读者对象是受过教育的普通公众,也包括多个领域的专业学者,这种写作体现了文理融通,展现的是有趣的科学文化、博物学文化。这已经超出了在不同科学学科之间架桥的努力,用古尔德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些年来,如这些散文所展示的,我设法拓展我对科学的人文主义‘描绘’(my humanistic‘take’upon science),把从一种单纯的实用装置变成一种真正的乳化器,使得文学随笔与大众科学写作融合成某种独特的东西,有可能超越狭隘的学科领域并使双方获益。”(The Lying Stones of Marrakech,2000:Preface 2)国人习惯于把它们视为“科普”,可是国内又极难找到对应物,于是又称之为“高级科普”或“科学与人文”。后者的表述还凑合,前者则不很恰当。国内相似作品颇少是有缘由的,一是当下科学家群体人文修养有待提高,二是不愿写、不敢写,怕受到同行的鄙视。
看到眼前这个中译本,我立即想起田洺(1958—2016),心绪难平。如果田洺先生还在世,根本轮不到我来为此译本作序。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是通过田洺而知道古尔德的。田洺活到58岁,古尔德也只活到61岁,真是太令人惋惜了。田洺治生物学史、演化生物学史、科学文化研究,当过教师也当过官员,是什么机缘触动了他最早开始翻译古尔德的作品?田洺说是王佐良先生。翻译家、英国文学研究专家王先生对古尔德的散文评价很高(自达尔文以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中译本序3)。而我是通过刘兵而认识田洺的,后来在科学传播工作中多有往来。无疑,田洺对于译介和传播迈尔、古尔德、威尔逊的作品与思想贡献巨大。虽有个别翻译不甚准确(谁又敢说自己的翻译都是对的),但是如果没有田洺的文化传播工作,国人对古尔德等人的接触还不知道要推迟多久呢。古尔德的散文极为高雅,有人说他是散文写作的斯坦·穆西埃尔(Stan Musial,美国著名职业棒球运动员)。我不懂棒球,但确实知道古尔德随笔的几个特点:有思想、纵横交错、语句复杂。有些人站着说话不腰痛,喜欢说风凉话,以偏概全,全面否定前人的文化传播工作,宣称田洺的翻译“几乎每一句都有不同程度的翻译错误”,真的如此吗?仅仅从逻辑上想一想,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把每一句话都翻错,那也挺难的吧?这种判断是对译者、出版社编辑和读者的多重侮辱。
我想对此书的译者表示特别的敬意。译书难,译古尔德的书更难。听说译者用了三年时间才整理出这个译本。想一想,将获得的稿费能够养活自己吗?又如何养活家人呢?我没有责怪出版社稿费低的意思,出版社能出版这类翻译作品已经很不容易了。书价在中国相对便宜(跟吃一碗面、买一件衣服相比),出版社作为企业自己生存也不容易,但书生和学子还在抱怨图书太贵了;单纯靠涨书价来提高译者的稿费,恐怕不现实。面对手机、信息网络时代的浅阅读泛滥,单纯涨书价可能会令许多年轻人远离高雅文化,比如他们更加不容易接触到古尔德。有关部门能不能研究一下,想个办法,让国家和民间基金会对于优秀的文化翻译给予适当支持?在这方面日本做得比较好,我们应当学习。
2019年12月2日于北京西三旗
2020年5月24日修订
(斯蒂芬·杰·古尔德.彼岸:博物学家古尔德生命观念文集的末卷.顾漩,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