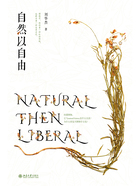
文化远比具体知识重要
布丰是18世纪的博物学家,是千年一遇的大博物学家。如今套在他头上的称号还有许多,如科学家、作家、启蒙思想家,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博物学家。就影响力而言,博物学家当中也许只有亚里士多德、老普林尼、林奈、达尔文、威尔逊等几个人可与之相比。
布丰对于知识的增长和人类对世界的理解有许多具体贡献,但最大的贡献是推进了“用优美的散文体来描写人以外的自然物”,空前激发了知识界对于自然世界的兴趣。布丰大规模地把植物、动物、岩石等自然物拉进了文学写作的范围,他出版的集知识、观念与文学魅力于一体的百科全书著作迅速成为时尚,对法国启蒙运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正名仍是必要的
布丰研究的博物学,法文写作histoire naturelle,涉及一个古老的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老普林尼那里,再往前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其大弟子塞奥弗拉斯特。布丰奋斗了半个世纪的大部头著作也称Histoire Naturelle,他去世前主持完成了36卷,后来其学生补充了8卷,合计44卷。这部大书的中译名应当为“博物志”或者“博物学”,却长期被不恰当地译作“自然史”或者“自然历史”。
为什么说那样翻译不恰当呢?博物学家达尔文、华莱士、迈尔、古尔德等人研究的内容不正好涉及大自然的历史演化吗?用“自然史”来代表他们所研究的领域不是恰如其分吗?非也!第一个理由是,以“自然史”来译犯了时代上的错误,相当于非历史地看待前人和前人作品。
在布丰的时代,演化思想并不是主流学术观点。他的辉煌著作虽然在个别专题上也涉及大自然的演化问题,但不是普遍的主题。对自然物的精彩描述才是布丰做的主要事情。这些描述,会偶尔碰到某物在时间进程中的变化,但是通常不涉及时间变化问题。就整个大自然而言,他更在乎的是空间、现状,而不是时间、历史。
对于现在的普通人士,以演化论(也译“进化论”)的观念看世界是相当自然的,因为大家从小接受的教育就一再提醒每一个人:世界是演化而来的,生命也是一点一点演化而来的,地球有几十亿年的历史。但是在18世纪初,人们并不是这样看世界的,即使那时的学术精英也不具备基本的演化观念。正是通过布丰、拉马克、钱伯斯、达尔文、赖尔这样的人物不断努力,学者才逐渐搞清楚演化的一般历程,在科学的意义上确认了地球的历史相当长。以今日的教科书为标准来看,布丰对地球年龄的估计是不靠谱的。但这样比较,意义不大。直到19世纪下半叶,学者们还在激烈地争论地球的年龄。地质学上常以百万年为单位计算年龄。100百万年是物理学家开尔文对地球年龄容许的最大值,而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认为恐怕要大于400百万年。实际上,按开尔文的精心计算,地球年龄逐渐在变小:1863年他估计上限为400百万年,1868年减小到100百万年,1876年减小到50百万年,1881年为20—50百万年,到了1897年他认定的地球年龄仅仅是24百万年(A.哈勒姆.地质学大争论.诸大建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1:122)。20世纪30年代,爱尔兰物理学家乔利(John Joly)依然坚定地认为地球的年龄不超过89百万年。而我们现在认定地球的年龄是46亿年左右。要知道,开尔文不是一般人物,而是有着巨大权威的著名数理科学家。科学界所认定的“事实”和“真理”,是随时间而变化的,我们不应当用今日的标准来要求前人。
第二个理由是,historia naturalis在西方很早就形成了一个重要传统,它是人类社会中记录、描述、探究大自然最古老的传统之一,一直延续到现在,名称也没有改变。布丰的工作就属于这个伟大的传统。理论上,这一传统的中文名可以随便起,但实际上不能那么做,特别是其中涉及一个古老的词汇“historia”(此拉丁词来自一个发音近似的希腊词),它在那时不是“历史”的意思,而是“探究、记录、描述”的意思。相关的作品一般译作“某某研究”或“某某志”,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塞奥弗拉斯特的《植物探究》、格斯纳的《动物志》、雷和威洛比的《鱼类志》等重要作品的书名都可以反映这一点。甚至培根的作品中还提到博物层面的研究(natural history)与实验研究(experimental history)的对比。其中的“history”依然是“研究”的意思,跟“历史”没关系。那么到了21世纪,有变化吗?没变化,学术界仍然重申“natural history”中的“history”没有“历史”的意思,不信的话可以读《哺乳动物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David J.Schmidly.Journal of Mammalogy,2005,86(3):449-456]。这几乎是学术常识,对此不存在任何争议,今日做翻译不能忽视这一常识。不过,并非只有中国人不注意英文词的古义,现在说英语的外国人也有大批人士搞不懂“history”的古义。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正像中国人也并非都清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中的“僵”是什么意思一样。旧版《现代汉语词典》甚至也给出了错误的解释,好在新版已经更正,将“僵”的错误解释“僵硬”改为正确解释“仆倒”。为什么说“仆倒”是正解呢?除了词源的考虑,还可从一阶博物上得到印证。观察一下北京山坡上常见的节肢动物马陆,就能理解它何以死后仍然不会倒下——因为支撑的脚众多!
第三个理由是,近代以来许多人就将“natural history”译作“博物学”了,可能是学习了日本的译法。这个译法很雅致,翻译讲究约定俗成。中国古代有“博物”一词而无“博物学”一词;日本有“植学”,而无“植物学”一词。两国交流中,许多名词汉字写起来相似,这是极平常的现象。不能单纯因为“博物学”三字与日本有关而不用。如果那样的话,“科学”“社会”“经济”“规划”“投影”这样的词我们还用不用?
许多人是下意识不假思索地译作“自然史”的,仅有个别人译错了还振振有词。一个看似有理的论据是,natural history名目下所做的东西与部分历史学家的工作方式比较相似,而与数理派的natural philosophy形成鲜明对照。也就是说natural history大致上属于历史派,而natural philosophy大致上属于哲学派。表面上看头头是道,清晰得很,但这种理解依然经不起推敲。以今人的眼光回头看,natural history的研究方式确实像历史学家的工作,特别是在宏观层面编纂自然物和人物的方式,与自然哲学穷根究理、深度还原的方式很不同。但是在遥远的过去,这两者都是哲学家合法的工作,亚里士多德和其大弟子塞奥弗拉斯特两者都做过,都可以称为真正的学问或哲学研究,在培根那里称为“真正的哲学”。说到底这种主张依然是用今日的想法改造历史。而且,译成“博物学”或者“博物志”,也并没有掩盖历史上两种或多种进路之间的差异。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不同进路,如今在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表现得非常明显,它们不同的科学观、科学编史理念受到空前重视,但这些并不构成重新翻译一个古老词组的足够根据。毕竟,我们得尊重历史。
也许,达尔文以后的natural history勉强可以译作“自然史”,大约对应于history of nature,但之前的那个悠久传统无论如何不能那样翻译。考虑一致性,并尊重传统,将此词组在不同的语境下译作“博物志”“博物学”“自然志”“对大自然的探索”“自然探索的成果”更为合理。类似地,伦敦自然博物馆、法国自然博物馆、美国自然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也不能写作“某某自然史博物馆”或者“某某自然历史博物馆”。如果不嫌啰唆,倒是可以写成“某某自然探索博物馆”。
如何看待以前学者的科学错误?
现在看老普林尼、布丰、格斯纳的作品,会遇到一个大麻烦。那些伟大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些低级错误!包括基本事实错误,也包括一些荒唐的观念。这的确是一件不小的事情。就知识的数量和质量而论,过去远不如现在,一些人以为科学作品会好些,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科学作品对事实、真相更在乎,我们现在读先贤们的作品反而更不容易忍受他们的糊涂、失误。
现在重新出版历史上的科学名著或博物学名著,就直接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无准备的读者甚至编辑、主编,大家都希望读到一部符合或趋于现代科学结果的作品。给青少年阅读的科学史名著,更希望传达符合现代标准的理性、客观形象。而在我在看来,此任务很难完成。特别是许多人同时还强调原汁原味、符合历史面貌地传达科学家、博物学家的形象,这任务就变得愈加没法完成。
在过去,不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努力,成功地传播了诸多科学家的形象和成果吗?没错,是很“成功”,但是不要忘记巨大的代价!我们绝对不要忘记以今人的认识来切分历史人物之工作的危害性。我们习惯于将他们的工作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与我们今日的理解有通约之处,一部分是坏的或不合格的,是我们今日不赞成的。那样做的确收获了我们想要的东西,却也破坏了历史人物的完整性、统一性。知识、科技在任何一个时代也都是当时整体文化的一部分,老普林尼、布丰等人的博物类作品自然而然比数理类作品更多地反映当时的世俗文化和本地信仰。作为一名尊重古人的现代人,我们能够理解并容忍古代普通人的荒唐,也要有雅量容许古代伟人(包括科学家)的荒唐。实际上荒唐不荒唐、正确不正确,并不是唯一要看重的方面。以教科书的眼光看,过去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错的,但那又怎么样呢?牛顿力学被相对论超越后它就不是科学了?如果那样,两百年后的后代瞧我们也不会好到哪里,在此可以学福柯笑一笑。不是嘲笑古代,而是通过笑来提醒自己。难道古代圣贤的智商不如我们?
具体到布丰的作品,应当怎样来阅读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先搞清楚布丰是什么时代的人物,在想象中把他的作品放到那个时代背景中来阅读,不要处处跟今日的教科书比。布丰说地球年龄为75000年,读者不能只盯着这个数字,参照今日的数十亿年来辨别布丰是否靠谱。还要看他是如何得出这个数字的,要将布丰的想法与他同时代的人的想法对比。要根据他的时代特点、他采用的证据和论证方式来综合判断他得出此数字表现了什么水准。某人从小的时候到博士毕业时,背诵的太阳系行星数都是9个,各级考试和公众科学素养测试时如果填下8个,都会得零分。到了2006年8月24日,太阳系行星变成了8个,之后的考试中如果继续填9个也会得零分。但是坦率点讲,数字填对了能说明什么?能说明填对的科学素养就高吗?重要的是了解到科学共同体在某个历史时期是如何认定行星的,他们根据什么标准判断谁是行星进而计算太阳系总共有几颗行星。也就是说,重要的是了解相应的科学文化(包括程序、方法和标准),而不是科学的结果——科学家认定的所谓“事实”和“真理”。因此,我的建议是要重视当时的科学文化以至于一般的社会文化,不要在一些知识点上过分计较作者对了还是错了、与今日的标准差距有多大。当然,专业研究者可以考虑得更周全些、分得更细致些。
通过关注作品所展示的科学文化、博物学文化有什么好处?读者可以在更大的基础、场域上欣赏、评析古人;了解他们首先是普通人,然后是历史上的伟人。否则,我们非历史地看待伟人,他们就显得非常异类,他们不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而是巫师或者大神。其实这并非仅仅针对博物学作品提出的要求,对于数理作品也一样,古人讲的原子、力、能、碱,与我们今日理工科教科书中的同名概念可能相差甚远,他们的许多观念、命题如果不参照当时的科学文化,也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但是,的确有些人,特别是有一定知识的人,无法容忍古代伟人犯低级错误。他们认为,出版古代作品,一定要纠正他们所犯下的科学错误。提醒这些人的方法是,可以先把前人的作品当武侠小说、游记之类文学作品来读。接着再思索一下,自己的智商是否真的高过相关的古人。最后,设想着把自己放回古代,如果自己是那位作者,能否写出更高明的作品?
经常有出版社邀我主持改编一套古代博物学家的作品集出版,读者对象为中小学学生,我都回绝了。我认为短期内没人能做到,长远看意义也不大。强行做了,没准副作用大于正作用,让一些初学者有理由嘲笑古代了,反而助长了其朴素实在论科学观。非要做的话,也要尽可能真实地展示古代作品的原貌,别做自以为聪明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当然,我并非反对注释和解释,译者、改编者多加些注释是有好处的,比如张卜天重译哥白尼的作品《天球运行论》(注意,不是《天体运行论》)所做的那样。不过,即使加了许多注释,古代的科学作品也非常难懂,这是必须注意的。比如牛顿的书、拉瓦锡的书,今日读起来非常费劲。“人人应读”之类的宣传,是可疑的。相对而言,达尔文、华莱士的书以通俗的英文写作,也没有数学公式,还算好读的,但是,他们的思想在19世纪几乎没几个人能够准确理解,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较多的人理解其演化论。历史上被误解最深的恰恰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有什么办法呢?想不出有更好的速成办法,作为读者只能一再提醒自己别自作聪明。
博物学的风格
瑞典的林奈与法国的布丰同一年出生,这实在是不小的巧合。林奈与布丰都是最优秀的博物学家,都为博物学的发展做出了一流的贡献,但两人的风格完全不同。
现在的科学家更欣赏林奈,林奈的“豆腐账”式书写与如今的各种植物志、动物志更相符。人们觉得布丰更像是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作品与现代科学的书写方式差别越来越大。再进一步,甚至有人觉得林奈更科学,布丰不够科学。其实,笼统比较意义不大,两人可对照的方面的确非常多,但很难说他们对科学、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谁更大。布丰本人不但在博物学上创造了奇迹,他在传播微积分、创立几何概率方面也做得非常好,“布丰投针实验”就是一例。显然,林奈无法与布丰比数学成就。就博物学这一行而论,布丰和林奈对博物学的目标、方法认知有着巨大的差异,但两者恰好形成了互补。“布丰的博物学并不是要对自然建立一个分类体系,而是要拥抱整个知识王国。博物学已远远不是林奈的图表了——因为在每个物种的名字背后,都有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并且与其他生命之间发生着各样的联系。”[朱昱海.从数学到博物学——布丰《博物志》创作的缘起.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31(1):81—85)]
林奈和布丰的写作方式后来都有各自的继承者,梭罗、缪尔、巴勒斯、奥尔森、利奥波德、狄勒德、贝斯顿、斯奈德、古尔德、卡森等人的作品更像布丰的,这些人大多与人文学术相关联,但利奥波德、古尔德、卡森也可算科学界人士。
当世界各地的自然志都编写得差不多时,全球范围的博物学家的地位都在逐步下降。每年发表若干新种,是林奈式博物学工作的延续,但在分子生物学的比照下,其地位已经远不如从前。博物学传统退出主流科学界,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也就是说,人们越来越不把博物学当科学看了,做博物传统工作的人想申请到科研基金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么,博物学是否真的就没现实意义了,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呢?显然不是,博物学仍然有生命力,但主要阵地恐怕要转移,此时布丰的《博物志》的写作风格将给人们重要启发。
博物学家(博物者、博物人)可以不是科学家,人们仍然可以做优秀的博物学家!布丰的写作风格在当今世界仍然十分需要,生态学、保护生物学、自然教育、新博物学,都可以向布丰学习。
到目前为止外研社的这个版本是最好的布丰著作选本。此书所加的《布丰传》、布丰入院演讲和生平简介都有助于读者理解布丰这个人。布丰在此书中讲述的具体知识,真的不太重要,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得到无穷多比布丰先进得多的知识。重要的是了解布丰的博物学文化、科学文化。
2016年3月15日于北京大学
2016年8月22日修订
(布丰.博物志.李洪峰,魏志娟,吴云琪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